徐兆寿新著《补天:雍州正传》走进北大
6月5日下午,“新人文写作与文化寻根——《补天:雍州正传》”品读会在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召开。北京大学陈晓明、漆永祥教授,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教授,青年批评家丛治辰、樊迎春以及中文系王思远、张闻欣、林孜等博士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张高峰,和本书作者徐兆寿,作家、该书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燧人氏工作室主任汪泉进行研讨。
活动由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区域与传统”工作坊共同举办,青年批评家丛治辰主持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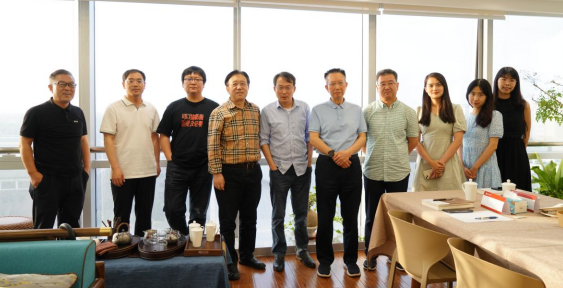
《补天:雍州正传》是知名学者、作家徐兆寿为家乡凉州书写的历史文化传记。徐兆寿以文学的笔触,以文化大散文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西北人的古今生活,是集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社会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一部关于大西北的百科全书,并融入了他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一部有情有义的传记。
该书分为三大部分,上部《天之道》回答了中国人关于天的问题。比如伏羲的“一画开天”从科学的角度讲开的是什么天,徐兆寿认为是时间和空间。那时候没有文字,人们就用天空中的星星作为指引,但星星没有形象和名字,于是人们便从大地或身边的动物、山川入手对天空进行命名,为宏观世界确立了时间和空间,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世界观。这是用今天的现代天文学可以证明的,所以这本书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天文学著作。
中部是《地之道》,也就是寻找伏羲在距今一万年和七千年之间是如何确立天道和地道的,是如何为天地间的生灵命名的,亦既天、地、人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元典《易经》。这一章就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来源,即昆仑山的确切方位,黄河的源头和神话诞生的地方。作者都用历史文本和今天的科学知识进行一一对应,来确立其年代、方位。最为重要的是,要找到大禹的九州,然后把重点放在最有争议性的雍州,为雍州立传。
下部是《圣人之道》,是对伏羲、女娲、黄帝、尧、舜、禹这些上古圣人进行文学式的立传,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式的回答。本书借今天人类所有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重新去伪存精,把上古时代留下来的一系列元典上的灰尘掸去,使这个天道明亮起来。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使古今沟通,中外融合,这就叫补天。一是重新补中国上古时代确立的天道,二是用今天的知识重新证明并确立天道。
陈晓明教授说,徐兆寿是站在今人的问题上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他认为天有缺,所以要《补天》。陈晓明教授讲述:“我在读兆寿过去的作品时,看到徐兆寿曾经狂热地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甚至科学。他在书里经常谈到尼采、海德格尔、福轲、德里达等,他还不停地谈论老子、庄子、《论语》《易经》《史记》《汉书》《后汉书》,还有《黄帝内经》等,但又不是掉书袋子式的,都是融化后的感想,有种古今、中外打通的感觉,至少他有这种通的理想。最为可贵的是,由于他是一位作家,所以他几乎大多数的篇章开始都是从日常生活出发,从我们熟悉而又有不同理解的现代材料出发,带入感很强,使本书显得深入浅出。”
出身于甘肃,后在北大教书的漆永祥教授说:“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时期设四郡、通西路,西路通中国就通,中国对外的渠道也是通的,西路塞,国内也不得安宁,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经验。兆寿出身于河西走廊,我出身于定西漳县,我们都带着对故乡西北的思考而行走天下。在阅读兆寿的著作时能感受到他的孤独以及那种很高的追求。他思考西北,就是思考中国,也是思考世界。”
“兆寿表现的这种情怀,这种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交织,同时具备了历史关怀和现实关怀,自己是很佩服的。”李洱说,“我看过他的《荒原问道》,后来又看他的《鸠摩罗什》和《西行悟道》,发现他谈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大视野、大叙事、大观念。在看到子思出现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结构,它通过作者跟弟子之间对话,对中国文化一些源头性问题、根本性问题做了重新发言,而且是对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现的一些疑难问题从整体上做出回答,我觉得这需要非常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化随笔,是钱穆式的,同时又是易中天式的,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知识、思想,试图做出一种自己的解释。”
丛治辰说:“我觉得兆寿老师是一个专门写奇书的人,《非常日记》《荒原问道》《鸠摩罗什》都有些奇,《补天:雍州正传》更是一部奇书,是一部非常规的书。这本书里面谈到了天文学、地理学、冰川学,谈到了《山海经》《易经》,有很多玄妙甚至神秘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有些深奥,而我则非常有兴趣。这种跨学科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写作了。另一个感受是它跟《论语》有相似之处。我读《论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种场景感,很生动、很真实。《补天》和《论语》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行走,它们是生活化的,不是在课堂上教书,而是一块生活,一起行走。学生遇到问题随时问老师,老师也有回答不上的,然后继续思考和回答。”
樊迎春说,在我看来,西部在这几部书中已经被徐兆寿老师对象化了,它已经开始成为一个被凝视的对象,需要凝视之后再重新阐释它,作为一个东部人,我对西部的所有想象都来自徐老师的阐释,这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鸠摩罗什》在我看来一是本小说,带有一定程度的文学的虚构和结构在里面。从《西行悟道》开始走入非虚构的讲述,他开始提出和找到一些溯源的方法,《补天:雍州正传》是又一次比较自信和大胆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说《西行悟道》还是在问一个终级的困惑:中国文化到底在今天还能不能给中国人以未来?还能不能说服世界并造福人类?从《补天》开始的那种焦虑和困惑以及怀疑和紧张都得到了本质性的疏解,徐老师开始以《论语》和柏拉图对话录的形式,直接阐释一个真理性的存在,这种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博士生张高峰、王思远、张闻欣、林孜等都谈了自己对本书的感受。张高峰说,徐老师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入手进入创作和学术的,这个路径在过去看是清楚的,但从《鸠摩罗什》和《西行悟道》开始发生转向,他开始从西部、中国文化、哲学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学术方向,可以说是跨越重重的学科屏幛,试图实现古今沟通、融通中外。我有幸在前年去过兰州,从兰州出发,穿行祁连山隧道到达武威,实地感受当地的自然人文的气象,那个地方是广袤的大地,有无垠的生命在生长。像徐老师这本书的《天之道》《地之道》,都是面向自然向度的悟道,进入到这样的生命空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自然气象,我们思考的肯定是和天地和生命有关的种种终极性的、本质性的、生命本源性的思考。这些思考也会自然而然从我们血液里面涌腾起来。
王思远谈到本书时说,《补天:雍州正传》中表现出的那种情感、情绪和孤独,让他觉得他和甘肃这个地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前不久有幸去了甘肃,实地感受了这个地方独特的自然风光,它的自然非常复杂,除了海洋之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它都存在。但在这样一个扩大的、复杂的地形集合体当中,它又有历史的症结,尤其当他们去凉州的时候,这个地方既有文化的扭结,也有战争的扭结,同时这里也是某种历史开始、某种历史结束的地方,所以自然的风光和历史的风景共同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心境。
张闻欣说,之前拜读了徐老师的作品,像《非常日记》,里面已经提出关于信仰的问题。到后来的《荒原问道》或者《鸠摩罗什》时,开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牵引到宗教和中国文化。到了最新的《补天:雍州正传》,徐老师更愿意把这个答案牵引到天道、地道和人道,天道是首要的存在,回到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圈层里面去寻找这样的答案。徐老师在数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对这样一个宏大且核心的问题,锲而不舍的探寻着。作品中有一种强烈的问道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并不是通过叙事,而是通过不断的思辨、碰撞、问答,来寻找一种终极答案。
林孜说,我想把徐老师这本书定位为一种对话录式的思想札记。为什么我要强调对话录?因为我认为您这个对话录恰恰反映了西方启蒙主义的姿态,西方启蒙主义有一个高位和一个下位,但是您和您学生的对话,是一种互相平等的对话,我觉得这恰恰契合您强调的《易经》当中没有过分阳刚的一方,学生也不是过分阴柔的,大家是平等的。
本书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燧人氏工作室主任汪泉说,本来我们相约写的是《凉州传》,结果兆寿兄交写的是《雍州正传》,是整个大西北的前传,也是凉州的前传,我觉得这也是奇缘。在我看来,这本书是真正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的一本书,是解开华夏文明源头的一把钥匙。本书《论语》式的结构是一个奇迹,至今还没有现代作家是这样写作的,这也是这本书一个极大的特点。
最后,徐兆寿表达了致谢。徐兆寿说,他的《荒原问道》《鸠摩罗什》都在北大开过研讨会,今天又是《补天:雍州正传》,这是北大对他的赏赐,他要铭记。他说,这本书可追溯到2005年,那时就已经在打腹稿了,但在一次次修改,直到疫情三年,他在家里研究了天文学、地理学、冰川学等知识后,对《易经》有了实体性的认识后,理解了上古华夏先祖的世界观、方法论、伦理观,于是便有了这本书。一定意义上讲,这本书是偶然的、天赐的。他还说,这本书之后,将写《开天》一书,这将是对《补天:雍州正传》的进一步解读。
- 2023-06-05【陇上学术铁军·第1期】张德芳:“简”阅人生 “牍”有滋味
- 2023-05-31微纪录片《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日常生活的独白
- 2023-04-11戏曲传承路上的“追梦人”——记第六届“感动平凉”诚实守信道德模范蒲虎勤
- 2023-03-21人物传记《裴正学的医路人生》捐赠仪式在武山县举行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