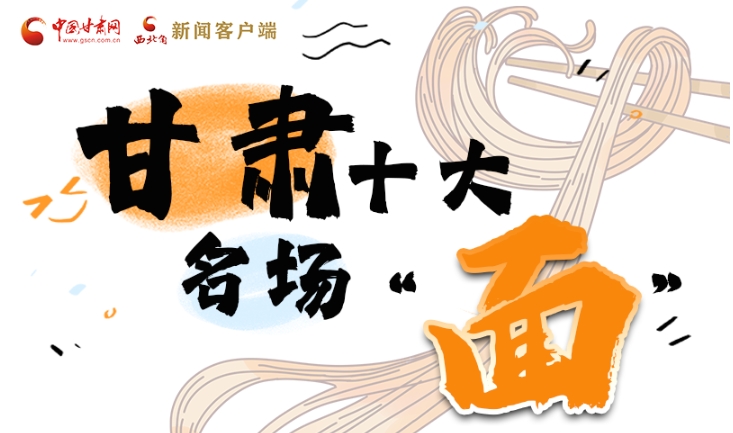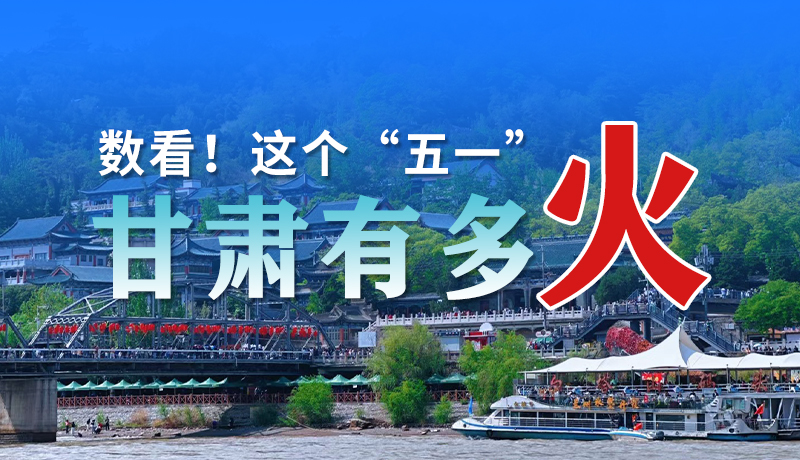【巡礼马衔山】《禹王书》:文明溯源、诗性智慧和诗性真实的有机统一
《禹王书》:文明溯源、诗性智慧和诗性真实的有机统一
郑莹
与当代其他作家类似,冯玉雷亦通过重述神话来实现社会关切、文化寻根、技艺创新和文化激活等目的,然而,强烈的启蒙主义意识已不再是当今“重述神话”叙事选择的核心主旨。《禹王书》的独特性在于,它巧妙地借助“重述神话”这一方式,通过文学审美的视角深入文明探源,从宏观层面介入并助力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与文化认同感的建构。更值得一提的是,冯玉雷成功地将神话叙述技艺与历史叙述笔调相结合,将历史考古、现实生活、民俗信仰等多元文化形态巧妙融入《禹王书》的审美视野之中,有效规避了当代“重述神话”创作中常见的“学术缺失”等弊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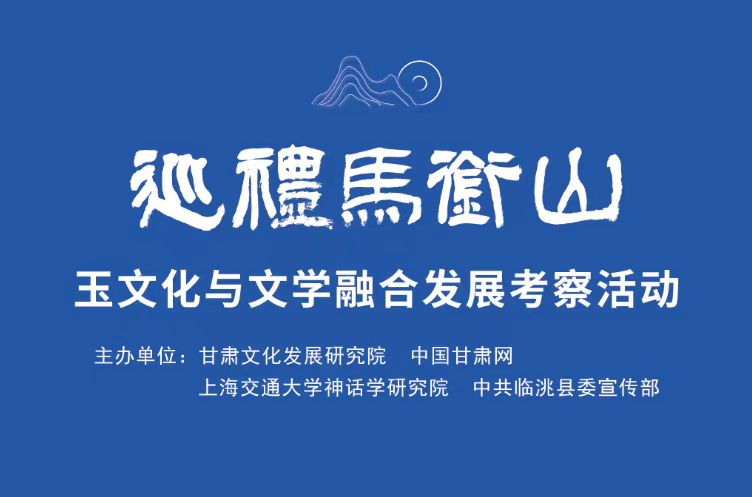
其一,神话叙述与历史笔调的互文性呈现。主要表现为不仅在神话叙述中巧妙地注入历史背景,同时也在历史叙述中映射出神话原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拘泥于史料文献、神话传说的“真实性”与“科学性”,而是在不失文学虚构色彩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古代史传文学创作技法,来实现神话原型和史料文献的跨界融通,最终达到一种诗性的真实。与苏童、李锐等作家的重述神话经验相比,《禹王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几乎涵盖了史前所有华夏神话原型。由于华夏神话具有零散性、片段化等特点,小说在时间和情节层面上的叙述往往出现断裂。然而,作者巧妙地借助文献史料等现实基础,作为文本的细节和“历史真实”,在增添文本文化底蕴的同时,有机衔接起大量神话片段,使整个小说叙述渐趋完整性和情节性。
例如,作者通过对夸父追日神话母题的置换变形,衍生出大禹与夸父之间赛跑的情节。赛跑途中,为了躲避共工,大禹发明了“禹步”。再如,作者吸收了史传文学中“述而不论,揭示规律”以及“众手成书”的创作技法,展演了大禹与女娲之间不同版本的爱情故事和民间广泛传颂的不同版本的重华事迹。此外,作者还以“禹赐玄圭”神话为叙述主体,寓言式展演了玉圭在中国礼制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小说中,黄帝曾送脩己一块形似玉圭的黄玉,并赐名为“耒锤”。一日,热恋中的脩己因听闻鲧牺牲的噩耗,戏剧性地误食了耒锤。因此,大禹出生时便手持耒锤。这一情节设定不仅为大禹的一生增添了传奇色彩,也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笔。通过山羌的叙述,作者将耒锤的历史追溯至盘古开天辟地时期,赋予了这一物象深厚的神话背景。后续,大禹不仅用耒锤在石头上创造了汉字“王”,还利用它成功治理了洪水。其中,大禹简化汉字“王”的情节,不仅体现了他的智慧与才能,也映照出他创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辉煌史实。
据唐启翠考证,玉圭作为王权神授和臣权君授的象征物,常用于权力命赐和朝代交接更替之时。治洪结束后,重华将磨损成斧钺状的耒锤幻化成玄色玉圭赐予大禹。在重华看来,玉圭不仅是大禹伟大治水功绩的嘉奖,更是他成为下一任天下共主的符信和重定天下秩序的圣器。在涂山会盟的盛大场景中,大禹手持玄圭站在台桑之上,接受各方诸侯的朝贺。玉圭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他权力的合法性,也安抚了众部落首长蠢蠢欲动的心绪。而大禹手持玄圭审讯防风的做法,更是暗含了“替天行道”的威严与正义。值得一提的是,涂山会盟情节中涉及的礼乐仪式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作者对《山海经》《礼记》《史记》等文献典籍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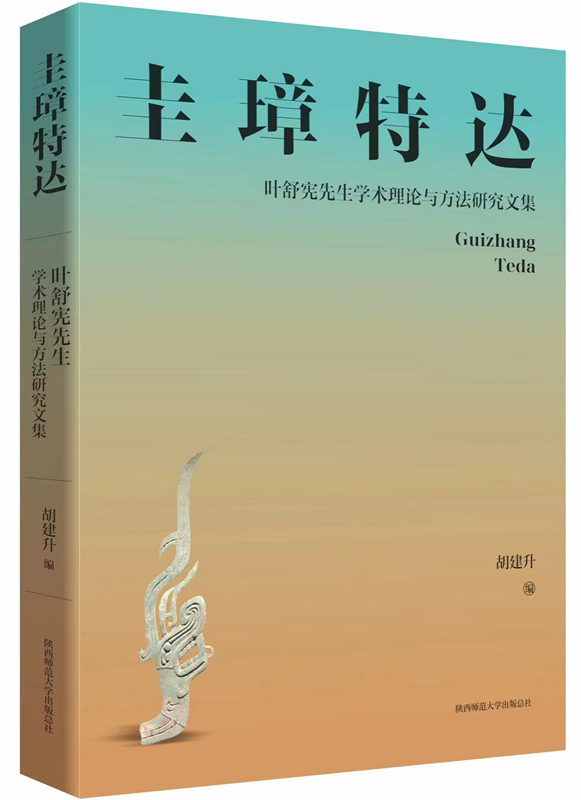
其二,作者在文化自信背景下,以文学审美的方式进行文明溯源,自觉寻求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跨界交流与多元共振。这种重述神话观念,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知识大爆炸情势下,作者对文学疆界的审视,以及自我创作个性的延续与拓展。从叙述内容的广博性和学术深度来看,《禹王书》无疑是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民族志。作者以史前信仰,特别是玉石神话信仰的演变为脉络,重新审视了整个史前华夏文明史,利用文学想象和跨学科交叉视野,宏观勾勒出华夏文明的发展图景,并将华夏文明溯源,讲好中国故事,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网系中,最终,形成一部集考古文物、典籍文献、神话传说、方物习俗、域外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为一体的《禹王书》。
例如,冯玉雷运用“活的文物”来唤醒华夏文化记忆,并利用文学想象将真实的考古背景和材料艺术性地融入某个特定的场景中,通过特定文物回溯和展现了史前精神文化信仰。正如叶舒宪所指出的,神话不仅能重现历史,更能激活文物。小说中,他创造性地将息壤神话意象与我国彩陶文化相链接,更将史前地母崇拜及生殖崇拜的精髓凝结附着于人形彩陶中。郭璞注《山海经》时称,息壤具有“自长息无限”的神奇特性。因此,鲧用“息壤”捏造出了富有灵性和生命力的陶器。小说中,冯玉雷以我国出土的史前女陶像为叙述原型,通过想象和联想等表现手法,将“活”的女陶像的文化符号与毓土生育时的生理感观变化相联系,生动复现了史前地母崇拜和生殖崇拜。同时,四目八瞳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各类陶器表情纹饰、文化渊源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进一步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此外,陶像上的黑红线条更随作者的想象生发,不仅出现在汉字的字形上,更点缀于后世器具的纹饰中。对于这种创作倾向,王宪昭在《感悟神话:激活人类文化传统的基因密码》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将文学创作植根于人类悠久的文明土壤之中,不仅符合当今世界文化多样并存的客观实际,更有助于我们在对考古史料进行文化溯源的过程中,重新感悟华夏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

其三,神话主体性复归及地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在“重述神话”的热潮中,神话元素在部分作者的“想象解构”“改头换面”中“面目全非”,逐渐丧失其文化主体性,沦为现实消费语境下的“快消品”。针对这一现象,叶舒宪曾批评此类创作倾向,认为“若是一味地迎合大众读者的趣味,片面追求市场销量,那么我们的重述神话就会剑走偏锋,助长‘无知者无畏’的时髦价值观。”并指出重述神话活动中的非学术戏说倾向,不仅与国际“重述神话”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创作者在驰骋想象力时也往往捉襟见肘,其作品的文化含量自然无法与其他优秀作品相提并论。
冯玉雷的《禹王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在还原神话基本样貌的同时,努力克服重述神话中文化含量不足的问题,自觉地将甘肃地区纳入其文学审美视野中,深入挖掘甘肃等西北文化空间所隐藏的神话记忆,并将该地域厚重、古朴的文化精神特质内化至神话母题原型的叙述中。在神话虚构与历史现实的同置并构中,甘肃地区已然被塑造成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神话地域。正如冯玉雷在《阳光、土地及发酵——关于小说艺术的对话》中所言,西部那变幻莫测的物象、色彩、气象和个性等,在刺激人生理感观的同时,其中所蕴含的能量和激情更容易将人带入那遥远的神话时代,沉浸于英雄史诗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作为深受西部阳光与土地熏陶的文化人,他的精神永远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例如,冯玉雷将敦煌三危山旱峡玉矿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母题进行了创新性联想。小说中,夸父逐日时,因饥渴难耐在月牙泉补充水源,却不幸被大羿误伤,最终渴死在野马南山以北、鸣沙山以东的戈壁滩,其躯体幻化成了三危山。夸父离世后,精卫每日衔三危山上的玉石前往东方换水,以此来纪念夸父。此外,冯玉雷还将大禹降生传说与“大禹出于西羌”的文献记载进行了艺术性联想创作。小说中,脩己生下大禹后便陷入了昏迷,是西羌女用羊奶救活了大禹,并教授大禹唱催奶谣唤醒了脩己。更值得一提的是,甘肃地区流传的饮食习俗也被作者巧妙地嵌入造字神话、洪水神话的叙述中。如他利用聚焦、全景延时等摄影技艺,生动地描绘了施黯制作西北面食的全过程,俨然为读者展现了一部“舌尖上的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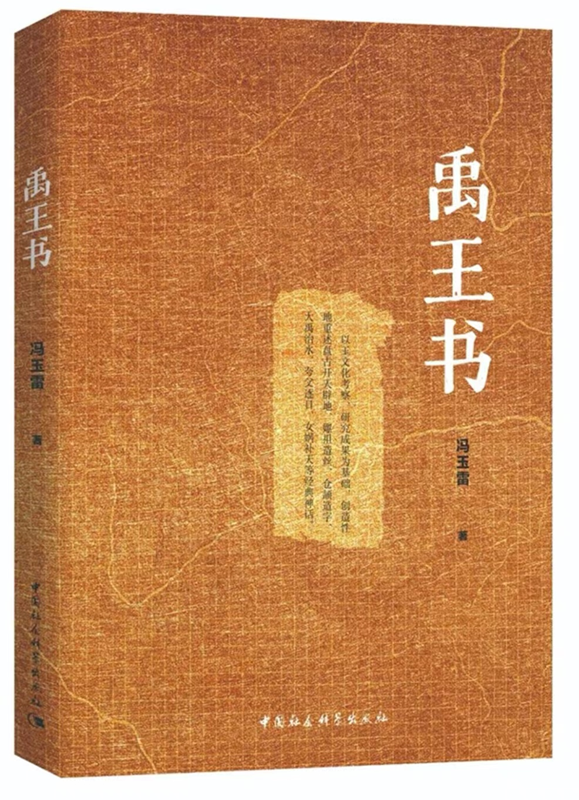
注:本文原标题《“重述神话”中探寻文化叙事路径——论冯玉雷的<禹王书>》,首发于《西部文艺研究》2024年第三期。转发时略有修改。
郑莹,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 2024-05-09【巡礼马衔山】冯玉雷:戈壁滩上的一片森林
- 2024-05-07【巡礼马衔山】金声玉振,玉说《禹王书》(三)
- 2024-05-06【巡礼马衔山】玉润华夏启文明——冯玉雷长篇考古小说《禹王书》印象
- 2024-04-30【巡礼马衔山】陆建芳:文学创作和考古学跨学科的拓展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