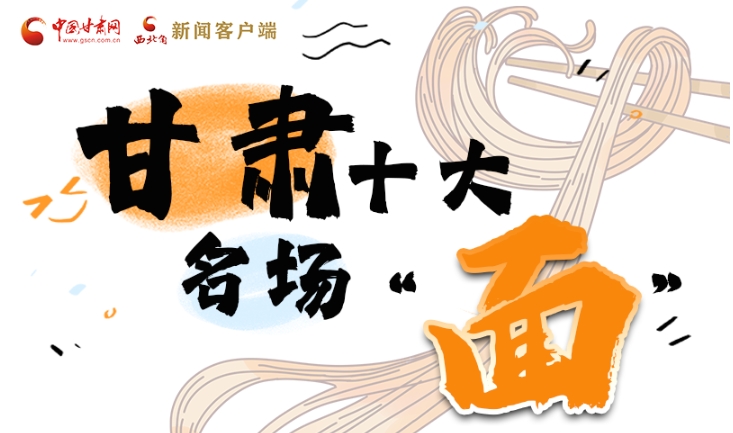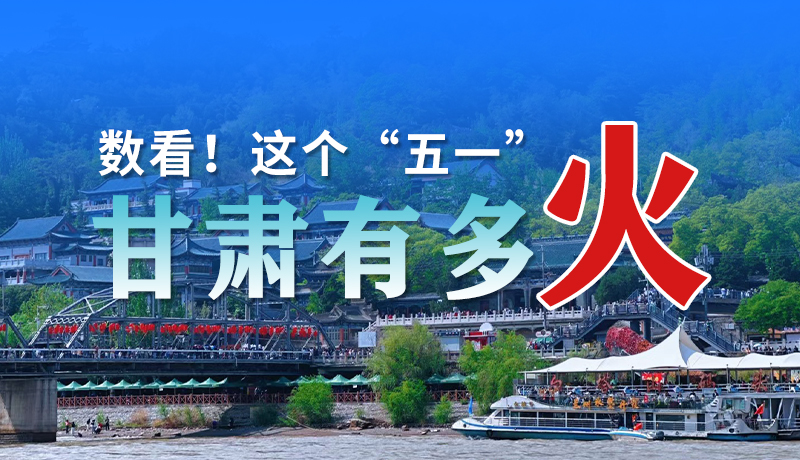【巡礼马衔山】《禹王书》:文化英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多元呈现
《禹王书》:文化英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多元呈现
郑莹
文化英雄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符号,沉淀着华夏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禹王书》中,冯玉雷细致整理了华夏远古时期的文化英雄,通过发掘文化英雄的形象与事迹,精心勾画出一幅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史画卷。他依照文化的传播演变路径,为文化英雄们构建了一个稳固的关系圈,并以“温润”的精神内核,贯连起整个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谱系。与此同时,他通过重塑文化英雄形象,使其充满时代气息,浓缩时代精神精华,从而彰显出时代的变迁。正如文日焕所言,文化英雄作为文化起源的承担者,在神话传承的不断发展变化中获得了新理解。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血缘系统,更是一个文化系统的象征。

一方面,表现为敢于牺牲、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的创业豪情。与《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那些尚武好斗,热衷于战功与荣誉,甚至视战死杀场为人生颂歌的英雄群像形成鲜明对比,冯玉雷刻画了一群为梦想而矢志不渝、忘我奉献、砥砺前行的文化英雄。
如为追寻“造字梦”而甘守寂寞、坚毅自律、矢志不渝的仓颉形象。仓颉年少成名,因卓越的才能被黄帝委以造字重任。作为造字者的代表,仓颉始终视造字为己任。造字途中,无论是自然界的洪水猛兽,还是安逸舒适的生活,亦或是诱人的“鹿皮裙”与谣言诋毁,都未能动摇他造字的坚定信念。此外,还有那些在平凡岗位上不甘平庸、恪守本职、尽善尽美的“螺丝钉”形象,如羲仲、施黯、鲧等人。在小说中,仓颉曾试图用权力和财富引诱羲仲放弃旸谷山的勘察工作,却遭其严词拒绝与驱逐;施黯因多次尝试研制面食而被部落首领驱赶,即便流浪至阆凤苑,也未能阻挡他研制新面食的决心;而鲧,作为新时尚的追求者,曾将神圣的爱情视作人生的目标,但为了传承非遗文化,他毅然放弃了这份美好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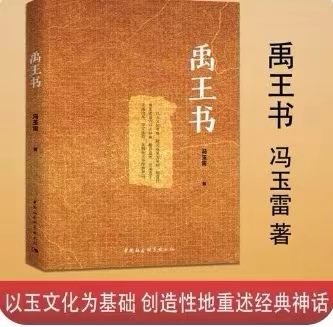
另一方面,映现为守正创新、疏堵并举、德主刑辅的创新精神。小说中,冯玉雷活化了故纸堆里沉睡的文化英雄形象,以“接地气”“生活化”的叙述方式,增添了文化英雄的烟火气,强化了他们的道德感召力。
如《禹王书》中,作者借仓颉、大禹、女娲三人的文字修缮与重述工作,生动展现了汉字的诞生及演变历程。文字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至关重要,甚至成为衡量文化是否进化到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汉字,作为当代中国居民最为熟悉的事物之一,其背后的故事与意义更是深远。小说中,仓颉以宇宙万物为灵感,为汉字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文字不幸被羊群误食后,大禹另辟蹊径,在历史的长河中依托“四重证据”反复求证所丢文字信息,最终完成了文字的修复工作,并简化了部分字形,使其更易于传播与使用。洪水爆发后,女娲肩负起打捞和重述文字的重任。在寻找文字的过程中,她悲痛地发现,那些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文字,在现实的“洪水猛兽”面前,竟变得面目全非、千疮百孔。作者借女娲的视角,以“文字”的畸变,隐喻了现实社会中邪恶念头对事物本质的侵蚀与损害。冯玉雷接受采访时曾称,博爱能针灸一切。因而,“爱”也成为女娲恢复文字生机、疗治迷茫人性的重要精神良药。它让文字变得更温润、更有韵味,成为慰藉民众历经洪水灾祸后焦虑不安、悲观忧郁心灵的重要力量。

此外,文化英雄的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造字事业上,还体现在治洪事业中,并成功将治洪过程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跨界应用于社会治理层面。以大禹为例,他推行的“九鼎行动”和《改道方案》都深刻体现了围堵与疏浚相结合的辩证唯物史观,彰显出高瞻远瞩的智慧与远见。在治理过程中,大禹根据局势变化灵活应对,对防风和义均等人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方案,既体现了公正严明,又展现了人性化的关怀。在治洪的艰难历程中,重华以宽容等美德为世人树立了典范,他深知宽容是化解仇恨、播撒美好的关键途径。因此,他对共工处于流放之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其反思与悔过的机会。而在新纪元之初,大禹则主张规范纲纪管理,实行德法并重的治理策略。他深刻认识到,人性的欲望是犯罪的根源,但仅仅依靠法规并不能完全根除人性的恶。因此,对于严重违法的防风,他果断处以死刑,以儆效尤;而对于罪行较轻的义均,则通过感召使其悔过自新,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英雄的精神内核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温润如玉”、海纳百川与美美与共的和合精神。冯玉雷将华夏文化史重要节点的文化英雄置于民族交流、跨时空对话的文化语境中,通过他们的形象与事迹,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文化特质。
首先,在个人层面,表现为认识自己。如鲧已超脱世俗流言的羁绊,学会了与自己自适自处。当遭受诽谤时,他回复道,不干涉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更无需为不实之词辩解。他坚信,胸无秽念,心骨皆清。其次,还表现为一种常与为善的人际关系。作者以鲧以死殉道的悲剧命运,间接揭示了网络世界中部分民众因断章取义、盲目跟风而导致的无节制情感宣泄,进而形成了残酷的“网络暴力”。为此,他呼吁道,民众应摒弃谣言与诽谤,用祝福的花朵和善意的话语来温暖彼此。最后,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一种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文化姿态,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定位。以仓颉为例,他曾担忧青铜的世俗气息会玷污文字的神圣性,因此拒绝将文字与青铜结合。女娲也表示,不想让古老温良的神圣纹饰附着在青铜器上。大禹就文化磨合过程中,那种试图规避一切新观念、新事物的“自我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纹饰的美好源自于淳朴的心灵和高尚的品德,不会因材质的改变而失去其本质。鲧也强调,“新文字”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不同文化元素会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冯玉雷更借四目八瞳之口,强调交织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状态。
注:本文原标题《“重述神话”中探寻文化叙事路径——论冯玉雷的<禹王书>》,首发于《西部文艺研究》2024年第三期。转发时略有修改。
郑莹,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 2024-05-09【巡礼马衔山】冯玉雷:戈壁滩上的一片森林
- 2024-05-07【巡礼马衔山】金声玉振,玉说《禹王书》(三)
- 2024-05-06【巡礼马衔山】玉润华夏启文明——冯玉雷长篇考古小说《禹王书》印象
- 2024-04-30【巡礼马衔山】陆建芳:文学创作和考古学跨学科的拓展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