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礼马衔山】《禹王书》:原始气息、现代情调与荒诞主义的巧妙融汇
《禹王书》:原始气息、现代情调与荒诞主义的巧妙融汇
郑莹
冯玉雷的重述神话创作展现了一种先锋实验精神,主要表现为在与传统浑融共生的基础上,尝试突破不同文体和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壁垒,在“原始气息”“现代情调”和“荒诞主义”的艺术张力中,探寻表现技艺、美学风格与价值观念的创新。这也彰显了当代作家试图通过精湛的文艺作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社会担当和文化自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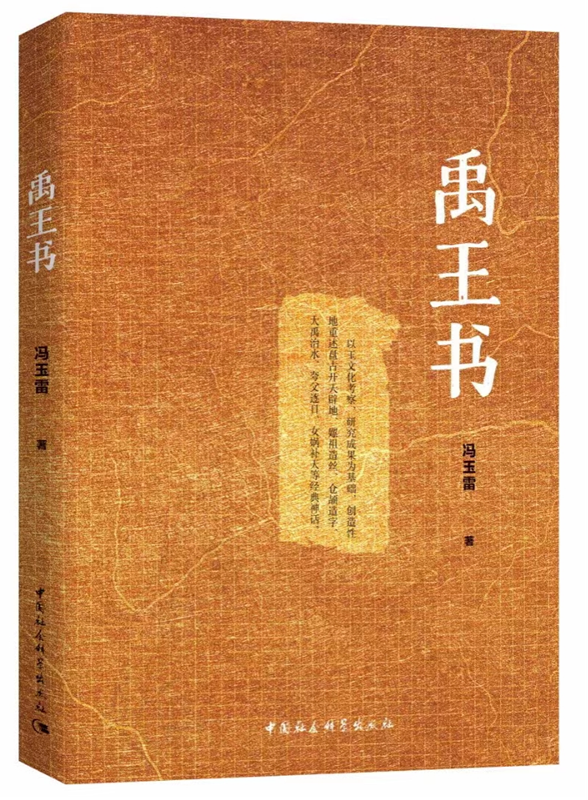
首先,直观体现为以神话介入现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神话是原始初民对自身无法掌握现象的解释。由此可见,除了虚构性这一基本特性外,现实性也是神话诞生的根基之一。在《禹王书》中,神话原型不仅成为连接众多文化要素的桥梁,更成为作者介入现实、观照人性的重要载体。
如作者借用了黄帝始祖神话母题,赋予“铜”这一意象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反讽意味。在小说中,铜不仅代表着物质实体,更成为欲望和外来文化的象征。部分部落首领对铜持负面看法,认为它是导致物欲横流、民风败坏的元凶之一,并且作为外来物的红铜对本土其他文化形态构成了威胁。四岳曾向鲧发出警告,强调玉石与彩陶的相互扶持是抵制铜文化扩张的关键,他坚信本土烧制的“陶”才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根基。然而,作者借重华之口,讽刺了片面看待问题的社会现象。重华认为,盲目排斥铜是一种虚伪且可耻的态度,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物质。他指出,物质并不局限于财物或外来物,自然万物如日月星辰同样属于物质的范畴。人类自古以来都在追求与物质和谐统一,既然铜器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了比石器和陶器更强大的功能,我们为何要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呢?此外,黄帝还曾用铜针治愈了毓土等人,而贩铜者也是通过合法劳动获得财富的,他们又有何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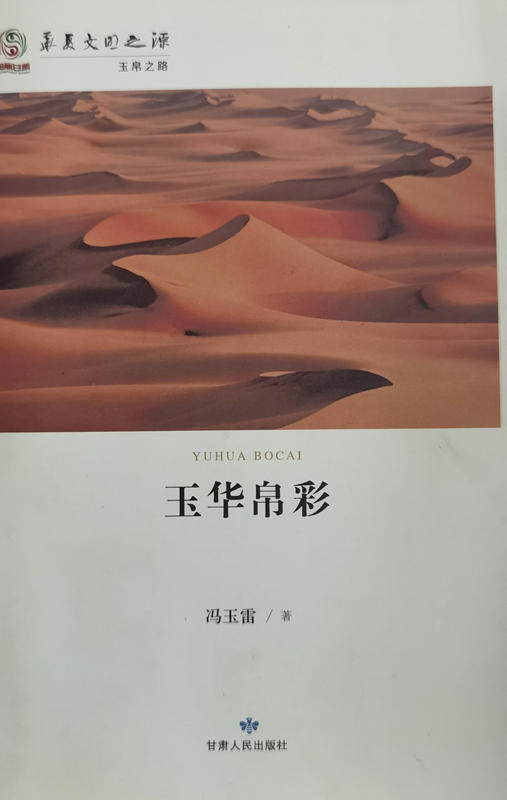
再如,冯玉雷将女娲造人神话和补天石神话与当代教育现状相结合。女娲将补天剩余的那块石头命名为“熊”,而“熊”又是启的乳名。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女娲创造了鸡、狗等牲畜作为陪伴。在初七那天,她用泥土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熊”。然而,在黄帝、桑林等人看来,这些泥人不仅需要满足合婚生育的需求,还应掌握各种技艺,如吹拉弹唱、耕作放牧等。但女娲认为,她所创造的“熊”应该是吃苦耐劳、儒雅有度等优良品质的继承者。女娲反驳黄帝的情节,实则巧妙地讽刺了社会中过分追求表面成绩,而忽略德育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行为,警示人们应当注重教育的全面性和长远性,避免陷入短视和片面的误区。
其次,梦幻世界的意识流书写是原始经验的映现。冯玉雷深受交感互渗神话思维的影响,他通过梦幻原型的置换变形,打破了文本的时空界限、逻辑框架以及主客体的对立状态。梦者思绪更同琴声、鼓声等动态声音表象互通共感,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交感互渗的超现实主义境界中,沉浸于原始主义的浓郁氛围和荒诞主义的独特基调之中。
以“美人幻梦”原型的置换变形为例,“所谓‘美人幻梦’,指用幻境或梦境表达情思与性爱主题的创作类型。”小说中,巨大的心理波动,如恐惧、悲伤、思念等,是梦者踏入梦餍或幻境的前兆。冯玉雷不仅将幻梦者的范畴扩大至所有角色,无论男女。还在情思与性爱主题的基础上,掺杂了神话预言的成分。如大禹与女娲初见之景,实则是大禹梦境的生动再现。如忧喜交加的巨大情绪波动,使女娲常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而她所梦之事竟都戏剧性地成了现实。热恋时期,她常梦到与大禹分离,最终,大禹也因治洪大业离她而去,被迫分离的两人通过鳌鼓声与梦境倾诉思念之情。又如,睡梦中的脩己随着嫘祖弹奏的《云门》乐曲,深陷逐鹿之战的梦餍之中。小说中,冯玉雷巧妙地将琴音的节奏与脩己的心理情感节奏相融合。起初,沉闷回荡的琴音为战前的紧张局势营造出浓厚的氛围。此刻,梦中的脩己恍若置身迷雾之中,呐喊、武器碰撞、骨骼断裂之声交织在一起,连绵不绝。冯玉雷通过大量短句的集中出现,直观展现了脩己恐惧无助的心境。随后,七弦琴在玉磬、陶玲等乐器的伴奏下悠扬响起,琴声浑厚灵动,凝重苍劲,梦中的世界也随之变得明朗宁静。顷刻间,平缓的琴声时而激扬,时而低沉,映衬出士兵们发现脩己时惊愕迷茫的复杂情绪。突然,琴声骤变,如泣如诉,如怒如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脩己在希望与挣扎中寻求出路的心路历程。最终,这场残酷的战争竟因脩己的突然出现而草率停战。更为荒诞的是,休战双方立即加入帮助脩己拼接铜纹饰的行列中。

最后,表现为“书”体及后现代含混拼贴话语方式的使用。冯玉雷接受采访时提及,现代文明的符号不断提醒他面对现实,然而,那些偶然映入眼帘的老城、废弃的大油罐等景象,不经意间又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原始本能与情感。为此,他决意打破时空界限,如同米罗一般,彻底“打破立体主义的吉他”,将众多原本不相融的元素巧妙地组织在同一画面中,追求它们和谐共存的理想生态。《禹王书》中,作者特意选择了书这一种自由度高的文体。与其他文体相比,书体在书写对象、文体规范及情感表达等方面展现出了无拘无束的特性。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记载,“书者,舒也”,“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

虽然其外表带有神话小说的色彩,但随作者书写对象的转变与情感的抒发,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散文、考察笔记、诗歌以及游记等文体特征。同时,随作者的发散联想,穿插许多史料文献进行解释性叙述。而与书体相对应的是,小说的语言体系也呈现出杂糅拼贴的特征。
如冯玉雷运用了跨媒介叙事手法,对神话传说原型进行了跨语境移植与现代演绎。小说中,传统的部落会盟仪式在现代语境下被微信交流平台所取代,朋友圈、公告成为各部落间信息互通、商业贸易的新途径。这种现代与传统的融合,不仅为故事增添了荒诞主义的色彩,也反映了冯玉雷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文明交流方式的深刻预见与反思。此外,冯玉雷还根据人物形象特征选择不同的语言风格。如时尚达人鲧常使用新潮词汇,展现出其前卫与潮流的一面;而恪守法制的狱官之长皋陶则常用“敬诺”“圣上”等词汇,凸显其严谨与威严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歌谣、文学片段、考古史料等多元文化要素的交融出现,增加文本陌生化效果的同时,对读者的文化积淀也提出了重大挑战。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需查阅相关文献,才能将附着在文本表面的意义释放出来。这种创作倾向,实际上是冯玉雷试图打破现代快餐式阅读模式,赋予读者更多阐释与注解文本的空间,进而实现文化科普与文明溯源的目的。

注:本文原标题《“重述神话”中探寻文化叙事路径——论冯玉雷的<禹王书>》,首发于《西部文艺研究》2024年第三期。转发时略有修改。
郑莹,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 2024-05-07【巡礼马衔山】金声玉振,玉说《禹王书》(三)
- 2024-05-09【巡礼马衔山】冯玉雷:戈壁滩上的一片森林
- 2024-05-11【巡礼马衔山】《禹王书》:文化英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多元呈现
- 2024-05-11【巡礼马衔山】《禹王书》:文明溯源、诗性智慧和诗性真实的有机统一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