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之州
雪在夜晚悄悄降落兰州。苍宇空旷,雪花纷扬,在橘黄的街灯下如蝶飞舞。北方的冬天太过瘦骨、单薄,天空便将雪做了花,俏扮世界。所有的雪花都像一个温暖的秘密,飘向各自的归宿。雪扮之后,冬天便可爱了,藏起了尖锐,掩盖了峭拔,满怀敦厚。
从兰州西站出来,天色未明。第一班公交车开过,垦出第一道车辙,清晰、分明,似划开了一条跑道,尚待脚步开启。停靠到站,乘客鱼贯而入。车厢冷清,车窗玻璃的寒气,把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一片氤氲。我擦拭后车窗的水汽,看着那道车辙在眼前一寸一寸远离,被纷杂的脚印涂成一片凌乱。
正是上班时间,街上的人们匆匆促促,奔忙在各自的烟火。西关十字,交汇着一路路公交车,卸下或带走各个方向的人群。雪在都市不是雪,是润滑剂,给逼仄的空间一滴清凉,急躁的人心一点滋润,它不在乎在人的脚下碾成雪泥。雪泥上行走的人们,伸出手,互相搀扶,互相挨靠,在雪的骨头上,掂到了人与人彼此的信任和亲切,宽容和慰藉。
我是一个先天孱弱的人,上苍便将一袭白衣披在我身,解除他人病痛,解救自身命运的劫,获得再一次救赎。陪病人走进兰大二院,安置妥当,身心顿时轻松。从医院出来,雪停了。对面清真寺拱顶上落了一层薄雪,一弯金黄新月静看尘世悲欢,鸽子飞起飞落,咕咕鸣叫。如果裁去拱顶下的人间,其上是多么童话的世界,所有的美好怀揣悲悯,羽翼欢动,将善良和爱播洒。
午后的阳光透过云层,光芒不耀眼,刚好够慈悲。繁华街头,熙攘的行人不断从身边经过。这是十二月年末岁终,所有人都在走向新年,走向下一个起点。拐过亚欧大厦,在常去的那家干果店,捧一把百合,拈几颗玫瑰,草木精髓散发的馨香,似吮吸到春天的味道。
走过中山路,尽头是黄河。中山桥是兰州黄河桥的标志。百年前,中山桥供人力车、马车通行。现在,它供看风景的人入画。百年老桥,百年期许,每一个螺钉都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一百年,够三生三世。前生、来世,一定也在这桥上,看黄河,看轮回,看红尘穿过一世一世的宿命。桥是佛手慈心,把天各一方相接,此岸彼岸,来来回回,渡过多少有缘人。
黄河北岸,白塔山有雪。我所知道的,白塔山一草一木都来之不易。土壤是运上去的,草木是运上去的,水也是运上去的。黄河厚兰州,薄幸白塔山。好在,一代代兰州人不辞辛苦,将寸草不生,换了一山苍葱。一根根引水管隐在不经意处,点滴浇溉。这一山的草木,都是绛珠草转世,一世一世的神瑛侍者精心呵护,轮回不停。或许,这是白塔寺诸佛的旨意。
经中山桥至白塔山公园上山。山路无雪,石阶干净,亭台廊榭,庙宇楼阁,幽深尔雅。西隅藏疏竹,照壁渡鹤影。曲径通幽,树荫蔽日,闹市里一处肃谧清净地。落雪藏在草地、花坛、树塘,枯草和落叶从雪中冒头,猛一看是一只只麻雀从雪中孵出。树丛、枝上的落雪,是佛手拈花。风不动,它挠着人了,漾下纷纷扬扬。不知什么鸟叫了一声,之后是久久的无声,想听它再叫,却没有了,耳边似还回荡着那婉转清丽,天籁回音。
望河亭远眺,兰山巍峨,黄河迤逦。每上一层,脚下风景都有细微不同。市嚣一分一分远,城市一寸一寸小,天无限无限大,河无边无边长。在兰州生活的人是中庸的,孤独时看山,失意时品水。人在山河间,站成一树草木。
山下看白塔,似是在天上,上到白塔寺,天却更高远。不大的寺院,只为白塔落脚。白塔渊源在元朝,重修于明代,七层八面。据说是为病故兰州的西藏萨迦派喇嘛而建。寺中三宝,象皮鼓,紫荆树,青铜钟。象皮鼓相传是印度云游僧所赠,毁于战火。仿制大鼓,由一头白象雕塑驮着,守着白塔。院内一株篷布遮裹的植物,大概是紫荆。青铜钟藏于白塔寺,康熙年间铸,不得见。寺院梵音清唱,佛香袅袅。因是寒冬,游人稀少,厢房上锁,只一个年老居士照应香客。白塔寺后,起伏的茆坡,随坡建有窑洞,柴扉半开,鸡鸣狗吠,隐秘了的桃源。倒是应了照壁上的题诗:“隔水红尘断,凌空宝刹幽;龙归山夕晓,鹤唳海天秋。”上山修行,下山江湖。大约那里的人,每天都庆幸自在:仰望山顶雪,欢喜在人间。
日影西斜,云层淡薄,阳光像爱一样穿透,抚摸每一寸大地。雪后天霁,如我渴望的明天,晴朗明亮。对岸群楼大厦,兰大二院遥遥在望,与烟火人间一河相隔,此岸修行,彼岸救世。消除病痛与灵魂救赎,都不可或缺。脚下的滨河路,车流多起来,流动间,如水草摇曳,参差荇菜。与之并行的黄河,在夕阳中泛着荧荧的波光,像打开的一卷羊皮经。(弱水吟)









 中国舞剧《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国舞剧《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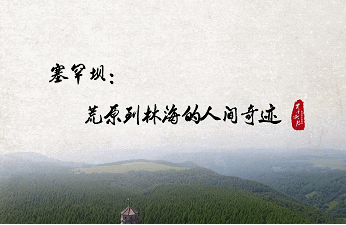 电影《那时风华》展现塞罕坝精神
电影《那时风华》展现塞罕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