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走索桥堡
夜走索桥堡
□王复库文/图

初冬的一天,我们沿着古丝绸之路北线前行。穿过平川区水泉堡大峡谷,翻越裴家堡岘口,进入哈思山原始森林地带。大雪纷飞,汽车在弯弯曲曲的砂硌山路上艰难爬行。
快要和索桥古渡见面了,我们激动不已,思绪似窗外的雪花,在哈思深林中飘舞。
到达靖远县石门乡哈思吉堡,天完全放晴了。哈思吉堡离索桥古渡东岸15公里,我们弃车步行继续向目的地挺进。
一个70多岁的祁辉老师,一个60多岁的祁有荣老师,为我和儿子带路做向导。
谈起索桥古渡,祁辉老师有说不完的话题。祁辉老师在当地中学教书,研究索桥古渡50年,曾站在哈思海拔最高的山顶看黄河落日,感受张骞翻越哈思山,沿索桥古渡过黄河的传说故事。
索桥渡口东岸的哈思吉堡,蒙语意为“玉也”。《康熙志》载:明隆庆六年(1572年)建,凭势筑堡,三面陡峻,是称天险。寇或入犯,迄不得逞,诚战守重地也。哈思吉堡先是管辖和护卫古索桥渡口、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畅通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堡寨,后又有防御兼驿站功能,明末开始成为一个大型商贸交易市场,陕商、晋商络绎不绝。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两省7府30个县商人捐资修路时立于索桥桥东的《山西修路碑》载,索桥古渡东岸的哈思堡当年有大车店18家,是商旅过境休息和货物交易之处,有店费“日收斗金”之说,可见其当时的繁荣程度。
山路弯曲,我们先沿沟壑前行,再翻过数座山梁,再沿沟穿行。我不知道古代军旅、商旅们是怎么走这条道路的。行走的意志力被摧垮了,我想回头。两位祁老师说:“现在回去的路比去索桥的路还要远”。我们只能跟着两位老人慢步前行。
太阳已爬上山顶,我们才来到索桥堡东岸。两位祁老师要赶着返回,留下我和儿子拍摄索桥堡遗址。遗憾的是,索桥堡沟谷深邃、阴山太大,索桥古堡遗址没有了光影。
站在东岸堡寨的石碣门上隔河相望,河对岸的古堡遗址黑沉沉的,峡谷阴影里的残垣断壁如同一支支军队在布阵练兵,暮色中的索桥堡古建筑群遗址静谧而神秘。
环顾四周,山峦峡谷沟壑里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仿佛连自己也不存在了,只有孤寂的黄水在空旷的峡谷中回吟。
我的心一下空旷起来,拍摄晚霞辉映下千年古堡的美好愿望,从梦中消失了。
没有拍到日落,我们对拍摄日出更加向往,毅然决定夜宿索桥堡。
天黑麻的时候,我们在黄河岸边一片野枣林里发现了一个小石头房子,破旧的木门,塌陷的土炕,屋顶的一半是露天的,这便是我们今晚的宿营地了。
深秋的夜晚,风大,星空格外明朗,星星漫延在芦苇荡中,洒在暗淡的河里。窎窎坡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声音在峡谷中飘渺,遥远得好像从千年汉墓中发出的呼救声。
风不停地在叫,河水在石屋后流淌着,呼啸着。
很累很困,却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仿佛有人敲门,声音很清晰,张骞骑着黑红色的马来了,几十辆马车拥到索桥堡桥头,要从索桥过黄河。不幸的是,车马行人全被匈奴挡在了索桥堡西桥头。双方对峙了半夜,索桥起火了,连索的24艘木船全被点燃了……风很大,火直往我身上扑,把我从梦中惊醒,拍拍身上没有火,静听是外面河水的声音。
由于一夜的梦中惊吓,我活动了一下,腿不听使唤了,撑着胳膊起身,身上全是土。
扒开蓬草堆,我和儿子背上相机拼命地向山边跑。太阳已晒到索桥堡西岸,拍日出的事被昨夜的恶梦给搅和掉了。
从石崖上艰难地攀爬了半个小时,才来到东岸堡寨的石碣门上。太阳光已跑过点了,我们赶紧架起相机,准备拍摄。这当儿,一朵黑云挡住了太阳,索桥堡遗址没光了,河面没光了。我们唯有坐在堡墙上叹气,只能等云去光回,太阳再露出脸。
索桥堡渡口是汉武帝时期开通的黄河官渡渡口,是古丝绸之路北线古渡群中最主要的渡口。汉武帝破匈奴收复景泰,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西进通道,而距索桥古渡15公里的媪围县城(今景泰县芦阳镇吊沟)的建立,又保障了丝绸之路北线西渡黄河各渡口的畅通。
索桥古渡横跨靖远、景泰两县。黄河东岸的索桥堡在今靖远县石门乡哈思吉堡西北15公里处,堡墙、石栈道、石台阶和石碣门遗址尚存。黄河西岸的索桥堡在汉置媪围县城西北15公里处(今景泰县芦阳镇境内),堡寨遗址尚存。
由于甘肃黄河北出口段属中原王朝与匈奴、吐蕃等西域民族长期争夺地带,在明朝以前,索桥古渡因战乱和朝代更替,权主历经频繁变更。索桥古渡曾是汉渡、唐渡、明渡的官渡渡口,也曾是匈奴渡、吐蕃渡、西夏渡。
索桥古渡一直是船渡或筏渡渡口。“索桥,名桥而实无之……索桥不过鼓棹浮舟,往来津渡而已……”。(《秦边纪略》)。明隆庆元年(1567年),古渡两岸间修建索桥墩柱基,用蓆子编制成碗口粗的绳索系在两岸四根“将军柱”上,再将24艘木船固定排列挂于绳索之上成为浮桥,索桥由此得名。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重修被河水冲毁的索桥,并在河东岸修筑堡寨铁锁关(堡址尚存),门上有碣,额曰“索桥堡”,驻兵防守,以确保渡口的安全畅通。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在河西岸的小坪上建索桥堡,堡内居民曾达300户。直到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南大道西(安)兰(州)公路开通之前,索桥古渡一直是丝绸之路北线进入河西走廊的必经渡口。清代乾隆后期,索桥古渡逐渐沉寂,北线商旅通过乌兰关、北卜渡西渡黄河。
现存黄河西岸的索桥堡遗址还能辨认出街道、院落、店铺、门楼等。堡城外的瞭望哨所、庙宇、烽燧、五座旗墩,渡口处“将军柱”台基和堡内石街石楼上的残垣断壁,怆然诉说着当年索桥商旅云集、古渡繁忙的辉煌景象。
历史是游走的。望着索桥堡石碣门上的雕刻,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吐番、匈奴在索桥堡残垣断壁的小巷穿行的脚步声。他们从不同历史时期走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者被贬谪,或者被杀戮……那时没人拍照,司马迁也未来这里采过风,索桥古渡没能进入《史记》,任凭恢弘的历史在河水和暮风中飘流。
河水是有记忆的。两千多年,岁月沧桑,朝代更迭,寨主频易……残缺的索桥堡就是历史上无数个辉煌的永恒,多少风云人物从古索桥这个历史舞台上走过,来去匆匆,人们来不急看清他们的容颜,就消失在涛涛黄河哀叹的回声里。
黄河与索桥堡又有着怎样的美丽错过?我们无法解开和还原张骞西渡黄河的历史密码。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第一次出使大月氏。传说张骞一行用了三天时间在哈思群峰中找寻最佳渡口,张骞登上松山极顶远眺,在诸多河湾峡谷中踩点,只有窎窎坡对岸有河谷沟壑,可通往西域,且哈思山松林繁茂隐蔽性强,满山遍野的油松,质轻利水易造船渡河。最终选择了窎窎坡上峡口为索桥渡口,西渡黄河。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索桥堡的残垣断壁上闪耀着魅惑而神秘的光芒,黄河像一幅金灿灿的油画挂在东西索桥堡之间,让人流连忘返。
只顾拍照,忘了身处无人区,忘了回家的路。
突然想起小口子村的友人石贵清先生,他会开三马子,拿起手机,没信号。我们想抄近道返回哈思吉堡。走到峡口时,两边万丈石崖,中间像刀切的一个石缝,峡谷险峻,无法逾越。
退回的时候,迷路了,走进一大片古坟地。暮色中,从远山峡谷中走出了一群绵羊,步子很轻,好像飘在云朵之上。羊群后面慢悠悠飘随着一个满头银发的牧人,远远看去像一只老山羊在暮色幻影中直立行走。
我们激动不已,声音放到最大分贝急切地喊到:“老大爷,走哈思吉堡有捷径吗?”
牧人摇摇头,恍惚间和羊群一起消失在远山的背后。
暮色渐浓,四野空旷,没有行人,没有归鸟,唯有西岸堡寨的那些残垣断壁在相互低语、凝视、交谈……
两千多年,索桥古渡褪尽了喧器与繁华,孤独和迷茫牵绊着它的灵魂,任何高端的摄影器材都无法拍摄它的内心世界,只有涛涛黄河日夜不停地守护着它的初衷,而我和沉重的相机只是索桥堡的过客。
风还在吹,手机还是没信号,天已黑尽了。
今夜,我们还得再宿索桥堡。









 中国舞剧《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国舞剧《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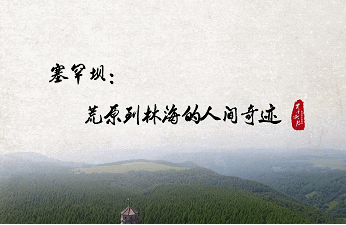 电影《那时风华》展现塞罕坝精神
电影《那时风华》展现塞罕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