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澈通透的白
澄澈通透的白
“下雪了。天明了。”母亲说。我惊喜异常,揉揉惺忪的睡眼,抬头朝糊着白色油光纸的木格子窗户往外看。咦!真个是白花花一片。抽门闩开门看瑞雪,是十分有趣的事儿。这雪不知啥时候落下的,此时继续悄无声息地飘着,地面已落有半尺厚的纤尘不染的白雪了。这白,白过小麦面粉,白过白砂糖,白得直晃眼。院墙南面的柴火垛上,院中部鸡笼顶端三四个花木已枯萎的盆子上,院北低矮的两间厨房上,几棵椿树枝杈间吊着的没剥苞皮的玉米上,成捆的红薯秧上,一人多高的拐尺形墙头上,无不被雪花簇拥覆盖。站在院子里赏雪,我瞬间成了雪孩子。
走出用槐树枝条编织的篱笆大门,眼前,是谁从银白色的雪地上扫出了一条条静谧的小路,通往牛棚、驴屋、井口、池塘,又连接到一家一户的大门口。本以为我起了个大早,孰料更有早起人。他是勤快的丁姓大叔,还是喂牛的赤姓大伯……我一一猜想着,虽没人告诉我是何人所为,但我知道,雪中的故乡肯定记得。
那年月,村庄里数百户人家的建筑,大多是低矮的草房,家境好一点儿的砖瓦房屈指可数。下雪了,除了村中的水井、喂牛的池塘,雪一落上去就融化得不见踪影外,环绕村子的土大路、磨坊、羊圈、牛棚、驴屋、柴草垛等,全都顶着厚厚的松软的白雪,身上仿佛披着既洁净素淡又雍容华贵的盛装。偶遇两三条白色或黑白毛相间的土狗在雪地里追逐撒欢,犬吠声很富于质感。雪不误人,人不误事。头顶一蓝底白花蜡染方巾,身穿碎花花红布棉袄的村姑,胳膊挎一笆篓筐粮食,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雪道上,到磨坊里去磨面。雪花追随着她的碎步儿飞舞,她扭腰转身送给雪花以欢笑和靓丽。老汉小心翼翼地从冬暖夏凉的水井口往上提水,站在滑溜溜的井台条石上,用力摇动“吱嘎吱嘎”响的辘轳把柄。肩膀上担着两桶冒着“热气腾腾”的清水,舀半瓢喝下,温温的,顿有荡气回肠之感。这雪天仿佛不属于寒冷,而属于温润。抓一把雪面搓手搓脸,起先凉冰冰的,一眨眼周身便热辣辣舒服极了。整个村庄端坐在澄澈通透的活泼泼的雪的世界里,一点儿都不感到寂寥单调。
村外,雪兀自飘落得纷纷扬扬,热热闹闹。天地皆白,银装素裹,一派妖娆。无垠无痕的雪野,静悄悄地消融了远山起舞的绰影和辽远空旷的地平线。天和地,相连相接,团抱成一个不容分开的整体。
雪天里,孩子们是闲不住的,他们有自己特有的乐趣。结伴在雪地里玩耍的群体中就有我。打雪仗堆雪人是不可或缺的游戏项目。好像不与雪亲昵,就会愧对从天而降的圣洁似的,尽管一双双小手冻得像红萝卜。我们有时还将泥土大路上融化了的雪水又结成的薄冰踩得啪啪响。悬空的大小窝窝里的薄冰,踩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如同音符巧妙的组合,抑扬有序,张弛有度。疯够了,穿着湿漉漉的棉靴回家,免不了被手中线密密缝的母亲呵斥一顿。自知理亏,刚一迈进门槛,便缩头缩脑溜进里间。
做了“错事”,也有弥补表现的机会。雪止了,碧空如洗,更显清冷。喜鹊、麻雀等鸟儿,争相从草垛间、屋檐下飞出来觅食,叽叽喳喳,招呼同伴。我们则学着大人的举动,清扫院落里和临近自家大路上的积雪。先将雪扫成堆,再用铁锨拍牢,端到树根周围,让树木过足雪水瘾,来年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家院中20多棵椿树、枣树、梨树,每到雪天都会受到如此特殊待遇。剩下的雪,还要端到粪坑内,同土末子、草木灰等废弃物混合沤成农家肥上地。村外铲雪的人群中,时常有我们的身影。风势作用,部分雪被刮到溜腰深的大路沟里。小小年纪的我们,扛着铁锨跟随大人一起劳作,将沟内积雪一锨锨甩到沟沿上方的麦田里,让正做酣梦的麦苗多加一床雪被。我们之所以兴致盎然,因那雪被下有我们望眼欲穿的颗粒饱满的麦穗,随风翻滚的麦浪,金黄灿然的麦囤……
夕阳西下,顺着田间小路回家。当看到雪后初晴的村庄里,从高低错落的烟囱中飘出的袅袅炊烟,向天空书写着平安和睦时,心中顿生惬意。雪中的村庄傍晚,闪耀着赏心悦目的艺术光芒,神圣而美丽。(刘传俊)









 中国舞剧《孔子》亮相莫斯科
中国舞剧《孔子》亮相莫斯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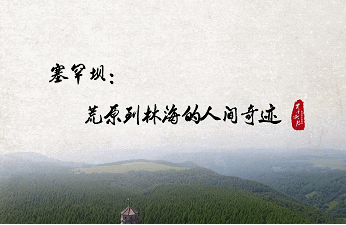 电影《那时风华》展现塞罕坝精神
电影《那时风华》展现塞罕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