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烂漫绽放时
你若烂漫绽放时
□韩德年
四月芳菲,在料峭春寒仍然缠绵难舍的高原绝对是一个奢侈的愿景。裸露了一冬的原野依旧萧索荒芜,只有蹲下身子,拨开干枯的蓬草,才会发现顽强的冰草芽从枯根中抽出的绿尖,怯怯地泛一抹春的羞涩。被刚刚播下麦种的田地,捂住自己贫瘠的胸,想把蕴藏了半年之久的不多的乳汁哺乳给冰冷的种子。一群红嘴鸦似一片油亮的黑云泛着红光铺到地里,啄食刚刚探出嫩尖的草芽,也啄食刚播下不久的种子;才出蛰不久的阿拉善黄鼠,用两只后腿人立在田埂山坡尽情地鸣叫——“啾啾啾啾”,那声音就像铁钉快速地来回划过玻璃一般的撕裂耳膜,却也给阒寂的山野传递了些许生机;远处山巅的山鸡不满黄鼠的嘶鸣,也不服气地“嘎达嘎达”絮叨不已;尖锐与圆润两道高音在空旷山野间绞缠碰撞,终于惹怒了空间的霸主,一只“黄健子”(隼的一种)似一页风筝,扑棱棱定在碧蓝的天幕,一串机关枪似的尖锐急促的鸣叫,似锋芒万丈的剑气掠过虚空,冰冷的肃杀让整个山谷霎间入定——山谷就这般喧闹在寂寥的春困里,慵懒中裹挟着躁动,闲适里暗藏着刀光。奋力生长的冰草大胆地吐了吐嫩绿的巧舌,仿佛在嘲笑动物们无谓的争锋。
我的入侵,打破了山间微妙的平衡。各种的鸣叫声戛然而止,静的瘆人的鸦群,蓦然爆发出一团裂帛般的嘎呀声。我翻过一道道岭,越过一道道沟,已到了山沟的最深处,不过只找到了几株锁阳根(这是我此行的目的)。当再次爬上一道平缓的岘口时,我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击懵了,一瞬间脑子一片空白,变成了一张立体的相片。我看见了一棵树,一棵杏树,一棵被绯红的烟霏笼罩的杏树!我苍白的语言无法形容她璀璨绽放的妖冶俏丽。宋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却觉这诗句里的杏花宛然是一个烂漫天真又调皮的豆蔻少女;而宋徽宗赵佶眼里的杏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又像是一位端庄娴淑眉锁愁云的宫娥。若是非要以人譬花,那眼前这夭夭灼灼婀娜似妖的满树杏花,更像是一位浓妆出阁的新娘。眼眸中盈盈洋溢着绮丽的憧憬,面颊上氤氲着妖魅的诱惑,云鬟低垂燃烧着青黛的情思。“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静谧山阿、明丽春阳、赤裸田野,全都沉醉窒息于她惊世骇俗的顾盼流眄间。没有嘉宾良媒,没有华堂云车,没有琼楼玉阁,没有礼赞喝彩,没有曼舞清歌,只有苍凉山隅,童秃垅亩,无垠之碧空,轻寒之东风。而她依然沉湎于似有还无的柔情幽思中,依然流光溢彩于瑰艳绰约的风韵里。寂寞中透着超凡的睿智,孤傲里尽是脱俗的赤忱,率意里诠释着生命自在的真谛,若水的柔美里却是一往无前无羁无绊的无畏。她收集了山野所有春光里的柔软烟霭,她涂抹了山野间所有的瑰丽华彩,她芬芳了山野中所有的馥郁幽香。她是行走在苍茫高原的寂寞剑客,她是舞蹈在天幕地台上的孤独舞者,她是荒原暮春里仅存的赤子。原野的春情因她的踟蹰山隅而一泻汪洋……
多少年过去,无情的时光湮灭了几多世道的丘壑,但那山隅里邂逅的翩若惊鸿的倩影非但未被磨灭,反而被岁月酝酿的更加灵动、活泼。我曾经几次再去山间,众里寻他千百度,而见到的不是一树葱茏,即是虬枝如铁,那如真似幻的绰约风姿却再也无缘得见。
找寻中,我在小区的院子看到了一棵楸子树,初冬的凛冽剥去了他一身的叶子,裸露的枝条上出现了一串串只有仔细看才能发现的楸子,仅有豌豆大小,刚看见时他呈殷红色,几天后颜色加深,到后来变得绛红。仿佛只有严寒才会加速他的成长。他们个头太小,味道酸涩,连院子里上天入地的熊孩子都懒得理他。但他依然一丝不苟的成熟着自己,尽情地在小雪季节里绽放专属自己的靓丽。我还找寻到了许多平凡的人,他们不以物喜,不因他悲,只在乎自己生命里的璀璨绽放,只专注自己内心天空的那片明媚阳光。他们都和山坳里绚丽的杏花拥有相同的徽章。
我忽然顿悟,既然他们是行走天地间的独行者,是隐身山阿只为顺应自然而自然的精灵,是纯粹因生命绚烂而绚烂的纯粹者,又怎能苟同于凡夫俗子的浅陋粗鄙?又岂会因为我的仰慕而迎合出被仰慕的模样?又岂会因为他人的漠视而因之轻贱自己?
你若烂漫绽放时,任凭他荒郊野岭抑或冷淡漠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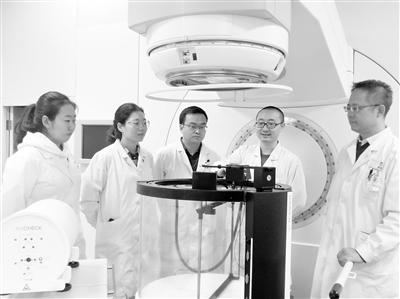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观影马拉松活动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观影马拉松活动 喜迎“十四冬”惠民文艺演出在呼伦贝尔举行
喜迎“十四冬”惠民文艺演出在呼伦贝尔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