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房亲戚 (小说)
远房亲戚 (小说)
作者:李骏虎《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3日 1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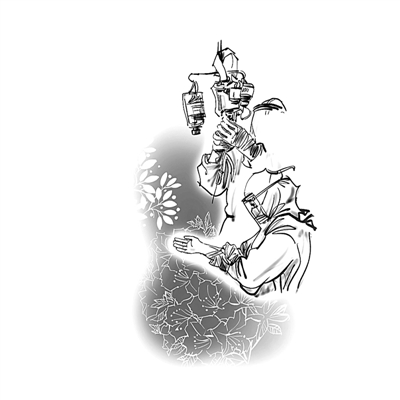
插图:郭红松
【中国故事】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远房表弟再没有打电话来,我想他一定宅在家里忙着冲牛奶洗尿布吧,我很想打电话问问他媳妇从湖北回来没有,到底没有打。……有几次,我仿佛从电视里有关湖北前线的报道中看到了他们写在防护服上的名字,可是一闪而过,不能确定。
又进腊月门了,2020年应该是农历的什么年呢?我不知道。从四十岁之后,我就对过年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总觉得还没做什么事情,又是一年过去了,常常会有生命的荒诞感。因此上,又常常羡慕那些个为生存忙得没时间去思考的人们,他们只要忙里偷闲地翻翻手机上那些短视频,就会快活得忘乎所以。尽管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过是一个放牛娃出身,但正是因为此刻是一个以思考为职业的知识分子,不免心里还是对那些个不爱读书的大多数隐隐地不屑。——人怎么可以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呢?我认定那些一心只为了自己活得舒适和快乐的人是没有情怀的,我向来对这样的人敬而远之,尽量避免和他们成为朋友。——不过,如果正好有这样的一门亲戚,那就没办法了。
远房表弟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我都没有接听,我清楚他找我什么事情。就在今年的中秋节,晚上我们一家去父母那里陪老人吃饭,我按照父亲的惯例慢慢地跟他对酌着,——父亲只有逢年过节和过生日时才喝酒,并且无论红酒白酒仅限量二两。母亲不住地给我夹菜,叮咛我不要光顾着忙工作,要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多吃饭。我“嗯嗯啊啊”地敷衍她,为了转移话题,开玩笑问中秋节老家的那些亲戚小辈里有没来给她送月饼的。没等我借机感慨一番世态炎凉人心不古,母亲笑着说:“你不说我还忘了,前两天你张村的表叔从老家来,提了十斤小米和一盒月饼,还在家里吃了顿饭,非要和你爸喝酒,吃了饭又喝了半后晌茶。小十年没来往了吧,猛猛地跑来,坐下不走,屁股真沉!”母亲说完撇撇嘴,表示嘲讽之意,又看看父亲,明显有事想跟我说,想让他帮帮腔。
父亲是个老实人,他端起酒杯和我碰碰,憨笑着说:“他找你有事哩,问我要你的手机号码,我没给他,让他有事先跟我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你有认识的人顺便帮他问问,没认识的人就算了,求人的事情不由咱,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母亲没指望上父亲,只好以退为进,“十年八年的连个电话也没打过,恐怕见了你都不认识,你说现在这人吧,都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母亲这是心疼我,怕给我制造压力,提前找台阶让我下。
我真的很烦总是因为亲戚朋友的私事去求人,我那些原本清清爽爽的关系,都因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去求人家关照而变了味,而我恰恰又是个崇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难免徒增了很多烦恼和精神苦痛。但是,我又知道母亲是个乡情很重而又热心的人,我不能不让老人把话说完,于是我故作不以为然地说:“张村的表叔?好像小时候见过这个人,想不起来了,他年纪不小了吧,能有什么事情找我呢?”
母亲马上来了精神,接茬说:“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一个种地的跑城里来能有什么事情?是他儿媳妇的事情,他儿子和媳妇都在城里上班,想找你换个工作。”母亲记性不好,平时也不爱动脑子,有些表达不清楚了,只好再次求助于父亲:“你给娃说吧,是不是这样?是换工作吧?”
我端起酒和父亲碰碰,等着他说话。父亲笑笑,为避免激起母亲的愠怒,尽量忍住笑意说:“不是换工作,是想换个岗位。他大概跟我说了,你妈没听明白,我跟你说吧。”父亲一讲,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位远房表叔的儿媳妇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医院上班,自医学院毕业后一直是外科病房的护士,外科是最忙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夜班还很多,年轻人累点没什么,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问题是,年初生了孩子了,产假一结束,工作规律照旧,可就顾不上照顾孩子了,家里和医院两头赶,眼见得脾气就不好了,夜班上到半夜,家里来电话说孩子哭得哄不住,就忍不住地骂她老公,自己也抹眼泪。家里想让她辞了职回家看两年孩子,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再找新工作,说什么她也不肯听,就爱干护理这行。于是退而求其次,商量了一下,如果可以调到体检中心这样相对宽松点的部门,矛盾就算迎刃而解了。可是,这样的大医院有好几百名护士,相对清闲的科室也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那几个,有谁从外科调到体检中心了,难免成为焦点新闻,其中的难度不比重新找一份工作更小。找我,不是因为我有多大能耐,我们老家有句俗话,“筷子里面拔旗杆”,这件事情落在我的头上,纯粹是因为我在这个以农民和普通人为主的亲戚圈里,算是“官”最大的。
我爸说完后,见我沉默不语,就责备我妈:“看,我就说别招揽这些个事情,隔行如隔山,他也不是什么行当的人都认识吧。”
母亲这个时候也慌乱不安起来,望着我的脸说:“我也没有应承你表叔啊,就是说先问问你,能不费劲办了就办,办不了咱也不欠他的不是吗?”
我看着父母内疚的样子,怕他们心里难过,更不愿意欺骗二老,就把实话说了出来:“巧得很,我跟人民医院的院长一起参加过干部培训,算是同学,我找机会给他打电话问问情况吧。”
“真的呀,那正好!”母亲脱口而出,她是个简单的人,高兴起来,“我打电话告诉你表叔?”马上就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一直在聊别的话题的人这时候也加入进来说:“妈,这事情没那么好办,谁不想调到轻松点的岗位?再说了,你知道有多少人认识院长?有多少人找他换岗位?他能都解决了?”母亲看看大家,不再说话了,低下头去吃饭。
除了热心和简单,母亲还是个执拗的人。中秋节已经过去好几个月,进了腊月门了,一天,我下班前接到我远房表弟的电话,他开车来单位门口接我,我就知道母亲最终还是把实情透露给了我那位远房表叔,表叔又报告给了他儿子。我在单位大门口见到了我未谋面的胖乎乎、笑眯眯的表弟,他恭敬而亲切地喊我“哥”,要开车拉我去喝酒。我晚上正好还有个应酬,就让他开车把我送到地方。路上,我又详细地问了问他媳妇的情况,大概是紧张,他有点语无伦次,我很能理解他——求人办事就会丧失从容,我就是讨厌这种感觉——对他多少产生了一点亲切感。我期待他能用家乡话跟我聊天,唤起我对亲情的回忆,可他一直在说普通话,这多少让我觉得有点失望。下车的时候,我们俩加了微信好友,我告诉他把媳妇的基本情况编一个短信息发到我微信上就可以了。他表示一会再开车来接我,我说不必了,晚饭后正好想散散步,跟他再见。远房表弟千恩万谢地开车走了。
几个月以来,父母没有再过问这件事情,——母亲从来不是个能沉得住气的人,我知道一定是父亲不让她问。而自从应下这件事情后,我也曾几次从手机通讯录找出我那位院长同学的号码,因为担心给他制造难题而最终没有拨出去。远房表弟用微信把他媳妇的基本情况发给我之后,我编了一段话准备发给院长同学,希望他能考虑一下该护士目前的家庭情况,毕竟在哺乳期间经常上夜班是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情,调整岗位是解决实际困难的最好方式。我一再修改我的措辞,希望帮他想出一个好的说法来避免引起麻烦。我甚至做好了他直接拒绝我的准备,——也许那样更好,我至少会给父母一个交代,表叔和表弟最多说我面子不够大,也比院长答应办事而给医院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好。但我又于心不忍,一个正在哺乳期的护士,天不亮就要去医院照顾病人,还经常要把小孩子放下去上夜班,在常情常理上真的值得同情,就算不是远房亲戚,我也应该帮帮她。
然而我最终没有给院长打电话,也没有把编好的微信发给他,不是我个性纠结,是我不确定还有没有别的护士比我这位亲戚处境更困难?还有多少?我能确定的是我那位院长同学肯定无法满足所有护士的换岗要求,毕竟多数的科室都是很忙很辛苦甚至很危险的。众所周知,教师、医生和护士注定是付出最多的职业,我们除了给予他们尊重和敬意,实在是帮不了他们什么的。
远房表弟不断地打电话进来,我都没有接听,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说。后来表叔也打,我说现在正忙着,回头回复他,也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我知道表叔一定在不住地催促我的父母,可父母却没有再跟我提起这件事。这反而让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我平时忙,但坚持每个星期找时间去父母那里陪他们吃顿饭,这次已经有半个多月没去过了。
春节到了,我知不知道2020年是什么生肖,都得去陪老人吃年夜饭。小年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说除夕一起吃年夜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舌头底下压不住半颗米”的母亲依然没有问起那件事情,我并没有因此而释然,相反心里怪怪的,仿佛体味到了他们淡淡的失望。但这一切突然间都不重要了,——曾经在电视新闻和手机微信中引起过大家注意,后来又被抛之脑后的武汉肺炎事件,一夜之间又卷土重来,被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成为了这个春节的主要话题。就在人们正观望和众说纷纭时,除夕的前一天,武汉封城了,雷霆万钧的疫情防控工作在每一座城市和每一座村庄展开。我们这座城市也启动了响应,住宅小区封闭管理,走亲访友都改成了电话和微信拜年。年夜饭当然吃不成了,除夕的晚上,我给父母打电话嘱咐他们尽量不要出门,在小区里散步时一定要戴好口罩。母亲遗憾地说:“我包了这么多饺子,你们兄妹几个都吃不上,这让我和你爸吃到什么时候啊!”
流年不利,大疫荼毒。初一照例收到应接不暇的拜年短信和微信,我忙不迭地抽空回复着,就看到我那位院长同学发到同学群里的祝福短信,说他此刻正在机场,很荣幸担任了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领队,即将带队飞赴武汉抗击疫情,送出祝福的同时没忘警告同学们做好防护,“你们做好自己的防控,宅在家里就是对我们一线最大的支持,众志成城、国泰民安!”院长这样写道。我很感动,忍不住拨打了他的语音通话,没指望他有时间接听,却听到了他惯常的理性而欢快的嗓音,不像即将以身犯险,听起来跟平时刚出手术室给大家回电话一样轻松。此时疫情汹汹,网络上的漫画家已经把新冠病毒描绘成了魔鬼的样子,普通人谈武汉而色变,因此我毫不夸张地对他说:“你就不怕啊?你这要放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是敢死队队长,是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啊!”院长嘿嘿一笑:“怕有什么办法,咱就是干这一行的啊。我还是个年轻医生的时候就参加过抗击‘非典’,有经验,没事。”
我鬼使神差地说:“你们医院还有我一个亲戚呢。”
“是吗?没听你说过啊,男的女的?医生还是护士?”
“女的,在外科病房当护士,等你回来我把她情况跟你说一说。”
“外科病房?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人民医院好几百护士,他这个院长肯定认识不了几个,为了让他提前有点印象,就把名字告诉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喊了起来,一连喊了两次这个名字,一次后面是问号,一次后面是感叹号,完了很大声地告诉我:“这个护士我认识,她是好样的,在我们医院所有护士里是第一个报名支援湖北的,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是你的亲戚啊,那她给你们都争光了!”
我始料不及,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冒了句:“那,她家里知道吗?”
院长说:“我听她们护士长说,她是先报了名才告诉的家里人,——我们这批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刚刚她老公抱着孩子来给她送行,看见她抱着孩子掉了两滴泪,又把孩子给老公了。嗯,孩子那么小,挺不容易的。”
我趁机说:“是啊,像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动员她不要去了?”
院长笑了:“这算什么,我们这批里面还有家里老人马上进手术室的呢,不是也去了?不瞒你说,我爱人还病着,儿子在外地回不来,我只好把她交给她母亲照顾了,她母亲都八十多了啊!”
他突然不说话了,良久,清清嗓子说:“先这样啊,要登机了,回来见吧。”
我想叮嘱他做好防护,想想他是专家,就说了句:“老兄多保重啊,回来叫上几个同学们陪你喝酒,给你庆功!”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远房表弟再没有打电话来,我想他一定宅在家里忙着冲牛奶洗尿布吧,我很想打电话问问他媳妇从湖北回来没有,到底没有打。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可以戴着口罩去上班了,一个人开车走在路上,我也曾想过给我的院长同学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又怕他正好在重症病房,到底也没打。有几次,我仿佛从电视里有关湖北前线的报道中看到了他们写在防护服上的名字,可是一闪而过,不能确定。
那之后,我一直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知道,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有时候手机铃声响起,我下意识地希望看到是远房表弟的来电,然而他至今也没有再打过来。
(作者:李骏虎,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曾获鲁迅文学奖)
相关新闻
- 2020-03-17我想与你来一场约定
- 2020-03-17曾尽匹夫责,不负少年头
- 2020-03-17挺住,我把外公和妈妈都借给你了
- 2020-03-17感谢生命中的每一次困难






 《我不是购物狂》
《我不是购物狂》 2020埃及中国春节晚会在开罗举行
2020埃及中国春节晚会在开罗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