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修订本)
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修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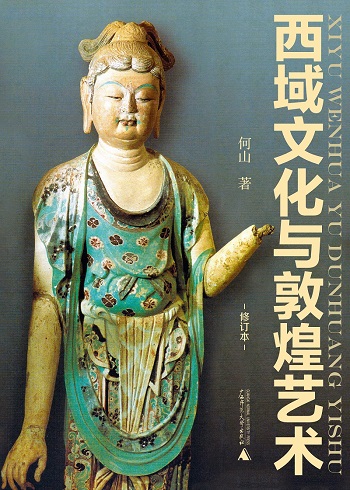
【基本信息】
书名: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修订本)
著者:何山
书号:978-7-5598-2324-3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定价:29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世界美术史的角度,从文化比较学、艺术哲学与美学的角度,对敦煌艺术的源流、题材、表现形式和风格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论证;同时对敦煌艺术的分期、发展、演变,以及各时期的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作了详细的分析。书中附有大量的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艺术作品,以及敦煌各时期艺术的经典之作,供读者参阅和比对,以期作出自己正确的思考与判断。敦煌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使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艺术相碰撞、相交融、相汲取,凝结成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产生了独一无二的、综合性的艺术群体和新型的文化艺术形态。
【作者简介】
何山,1941年生,湖南湘阴人,著名书画家。1964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壁画专业。同年就职于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的临摹、研究与创作工作。曾受教于庞薰琹、张仃、吴冠中诸先生,深受他们融古参今、博采众长、转益多思、构建新型文化形态的治学精神与美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传统艺术有深刻的理解,对西方艺术亦了然于心,强调艺术家的生命全在于作品。创作壁画作品《黄河之水天上来》《楚魂》等;岀版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何山卷》《何山作品选集》《百体篆书千字文全解》《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等。
【精选书摘】
张锡坤序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何山先生的《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出版至今已20年有余。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部著作非但未因时间的推移而稍显陈旧,展读之下,反倒每觉满眼生机。
何以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起,敦煌学即迅速成为世界显学。千载宝藏的重见天日,着实令人目眩心动、意往神驰。1964年,大学甫一毕业的何先生,正是怀着无限的好奇与梦想,毅然决然地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专业本行自然是视觉艺术创作和风格学的研究。但敦煌学因牵涉到文献、历史、宗教、语言、地理、民族乃至交通、科技等学科纷繁的头绪,因此关于其中的任何一项研究,若不甘心筑塔于沙,就必须从头做起。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的敦煌学处在一个文献整理和研究译介的基础性工作阶段。学界从头做起的“头”,一般来说包括一远一近的两个。“远”者为敦煌西域地区的古史地理及其演变,“近”者为藏经洞的发现和紧随其后的西方探险家劫经、分藏与整理、著录和研究的概况。直到今天,敦煌学的概述性著作仍采用这样的背景叙事方式。我想在与诸多相关著述的比照下,来谈谈何先生研究路径和方法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舍近求远、直指本源的手段上。从上古以降西域的古史地理、人群活动、文物遗存及其精神气质,来牵动北朝以来敦煌石窟艺术的解读和辨认。就书名来看,论著的内容似乎分为“西域文化”和“敦煌艺术”两个层次。而实际上,作者恰恰凭借自己的努力,避免了同类著作那种涣散铺陈和隔靴搔痒式行文的无奈,而是以各种主旨性的意念,把这两个时间段的问题,打造成一个“互文”的系统,形成一种相互介入、两相辉映的论说脉络。让读者感觉到,著者是就思考成熟的“问题”——亦即一个充分的理解前提——来组织材料和展开论说的。
例如,关于敦煌壁画中的虎和鹿,学界或认为出自南印度的风格,或以为受到楚文化长沙马王堆帛画造型的影响。何先生则以早期西域乌孙、大月氏尤其是匈奴等游牧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再佐以内蒙古阴山、甘肃黑山、新疆天山南北大量动感十足、栩栩如生的岩壁动物画,断定这是卡拉苏克文化艺术的典型,亦即敦煌本土的艺术风格和民族精神的表达。这样的探求和释说,避免了那种支离琐碎、望影向壁的无稽之谈,令人深信不疑。
再如何先生借助古史传说和文献,讨论了关于中原和西域的交流以及河西走廊的开通问题。指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类似的活动既已出现了三次:一是大禹治水“至于西极”的传说,二是周穆王西巡的记载,三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由中原经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南下伊朗、西去南俄商路的开通。如果再考虑到匈奴对西部游牧民族的早期统一,那么“就不能说张骞是‘凿通’或开辟了中西要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将丝绸之道夺回到汉王朝的手中”。运用神话传说来探索古史,徐旭生先生曾以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树立了一个可贵的典范。而和徐氏相比,除了传世文献的运用,何先生更借助了考古发现的实物去印证传说。例如沿途发掘出土的中国丝织品、玉、金、漆、青铜器皿,对古史传说的印证,起到了无可置疑的支撑作用。
敦煌地属古雍州,见载于《尚书·禹贡》。何山先生对其地历史的探求,不仅借助古史传说,还上推至史前的马家窑文化,显示出永不止步、永不满足的追索精神。这种开阔的视野及其运用的有效性,不禁让我想到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时段的特殊价值”的思想。在布氏看来,传统史学对短时段、个人和事件的关注,造成了一种“急匆匆、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从而忽略了“构成科学思想自由耕种的全部现实和全部耕种的历史”,因而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在他看来,史学研究只有借助上升到阐释层次的长时段概念,才能获得与历史曲线对应的“新的参考点来划分和解释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长时段似乎是导向普遍观察和思考所有社会科学方法最有用的路线”。何山先生对包括莫高窟艺术时期整个西域文化的探讨,都显示了这种长时段的运用意识,克服了为数众多的论者那急匆匆、戏剧性、近视病和浅尝辄止式的讨论。我想,这种史学研究中的宏观视野的价值,并非他人所意识不到的,只不过更多的人在其史学研究中,缺乏那种对历史的诚心和敬意,未肯尽心费力于此罢了。
《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的宏观感,不仅表现在时间的维度上,更见于其空间上纵横捭阖的魄力。从而构成了长时段与长距离三维交错的意义系统。著者通过消解国内研究者普遍持有的中原文化和汉民族的本位观,将视线聚焦于西域自身,以此为立足点,环顾希腊、印度和中国中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往来汇聚与碰撞交融。在何先生笔下,西域这片亚洲腹地真正成为世界三大古老文明的辐凑中心和欧亚文化的枢纽所在。而敦煌之所以有幸接受三大文明浪潮的洗礼,除了地理位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其本土兼具了“混交型游牧文化”与“开放型商业文化”的精神气质,这使其“行为动力”与“心理目标”一拍即合,势所必然地成为华戎所交之一大都会。
在所有的论说中,作者时时不忘围绕“商业”这一主题。不仅三代时期西域一直承担着中西物产通流孔道的职责,匈奴民族的游牧活动在其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希腊、罗马的军事东征与文化扩张,也本于其自身先天的商业精神。更为别致的是,何先生探讨了印度佛教与商业的种种亲和性,对教以商立、因商行教的历史隐秘的发掘,直接指向了敦煌文化艺术之气质与繁荣的最后根源。我相信,每位读者都会被何先生那充满睿识和魄力的材料组织和叙事策略所慑服,对那曾经辉煌而又业已消逝了的西域文明产生无限的想象和神往。
何山先生是以艺术创作为本业的,由此转入到艺术史的探索。他能在西域文化研究领域做出这样的成绩,既实属不易,又理所当然。所谓实属不易,是就他广泛大量地阅读、消化和运用中西历史、考古、民族、交通的学术材料,最终织构成一部绵密且阔大的学术著作而言。所谓理所当然,则是指他的艺术生涯为其学术研究贡献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想象力!
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以严格的、经得起检验的史实材料来说话,这自不待言。但我更觉得,作为优秀的史家,尤为可贵的是他依据材料去阐释历史的想象力。前者为“史学”,后者为“史才”,二者兼具,才能促成真正的“史识”与“史德”。此中道理,正如刘述先所言:“历史是要通过史家主观的正确判断,来重新建构出客观历史的真相。既要辛勤地发掘搜集资料,更要把这些资料贯穿起来绘成一幅历史的图像,乃是一项富有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历史的事实和物理的事实不同,它是意义的单元,要通过解释和再解释的历程,才能保持它的意义,当解释停顿时,意义也就丧失,看不到它对历史的重要性……再进一步,这些意义单元必须贯穿起来,才能够给我们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图像”。
在何先生这部皇皇巨著中,想象力的火花随处可见。如他提出这样一个很少为人所注意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4世纪,亦即古希腊艺术由古风期到全盛期这个时段里,人物雕塑的服装,由质地较为粗糙、衣纹转折单调平直,转向了半透明质地且明暗变化日益丰富的表现手法?著者明确地回答道:“(一定是)中国透明或半透明的丝织、罗纱启发了古希腊雕塑家和画家的灵感,引起了希腊雕刻绘画表现手法的变革。”此说可谓极为新颖大胆,而谛审其依据,却毫不荒率突兀。因为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丝绸既已传到西方并享有盛誉,不仅贵族妇女着以锦绣罗绮,甚至军队中亦将中国丝绸制为旌旗。“也正是这个时期,即古希腊艺术全盛时期的雕刻,它的服饰,特别是衣裙的质地,开始变得轻松、柔软、贴身,呈透明或半透明状态。对极善于表现人体美的希腊雕刻家而言,中国的丝绸质地,更有利于他们创作理想的发挥,从而创造出更真实、更含蓄、更抒情的艺术作品。”
此外,如何先生由辛店彩陶的器型及纹饰,推断它或许是西域一支羌族部落的遗存,“羊角纹的普遍运用表明羊角纹有可能是羌人的族徽标记”。注意到西部半山型装饰中静态的方格和半静态棱形,是早期敦煌壁画中常用的基本纹样;而马家窑和半山彩陶运用的土红和黑色,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常见的基本色……诸如此类联想性论点的提出,既表现了作者独立和富于个性化的思考,也予人以启迪和想象力的再激发。何山先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我相信俄国绘画大师列宾的那句话:“灵感不过是顽强的劳动而获得的奖赏。”
最后,还想说说该书表现出来的著者那精湛的语言教养。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呈现出一种别有风味的叙事格调。笔墨时或洗练典雅,时或婉转流宕;庄重而不失生趣,绵密且气韵蓬松。很显然,作为视觉艺术家的何山先生,同时对语言的色调和气息有着一种敏锐的体验。在宏阔的材料综理和繁复的问题讨论中,不仅无一费辞,且不落同时代文本语言那常见的忸怩空洞的俗套。表现出超拔出群、落落大方的气度。尤其是他对三大文明艺术的描述和分析,能够去芜存真,直取要害,正所谓“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何山先生以他艺术家兼学者的优秀素养,以他的真情真性和真知真见,向学界奉献出了这部可贵的读物。
向何山先生致敬!
2010年9月18日
张锡坤,著名美学家,吉林省美学学会主席,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关新闻
- 2020-04-13报章里的中国记忆
- 2020-04-13柳斌杰:英雄与时代同在
- 2020-04-09深入生命本真状态
- 2020-04-09孤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