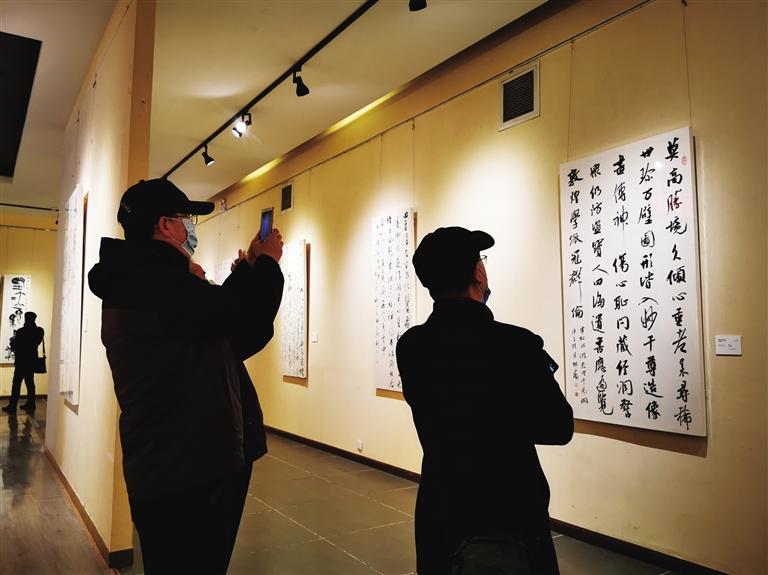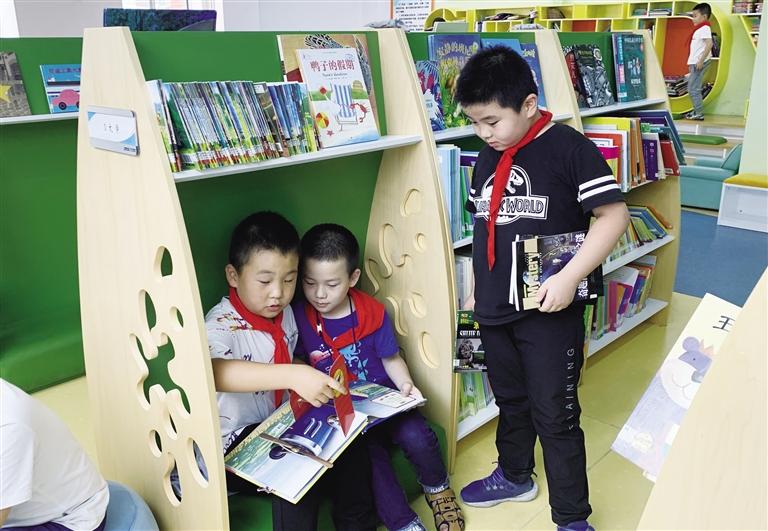不一样的蒸馍
不一样的蒸馍
我是吃蒸馍长大的。
蒸馍,或者馍馍,是西北一带对馒头的叫法,听起来有点土得掉渣,实则富有民间气息。小时候,母亲不是做蒸馍,就是烙大饼——乡间的叫法是锅盔。她很少做豆腐粉条馅的包子,那是逢年过节的事。西北人的蒸馍,是贫寒人家的口粮,出远门时会往行囊里塞两个,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我吃过的蒸馍、见过的蒸馍,都是平底、上呈圆形。后来,在平凉泾川吃到了一款不一样的蒸馍:罐罐蒸馍。
那一年,忽然来了兴致,满甘肃乱跑,行至泾川,遇雨,借宿于一户农家窑洞。晚饭时分,主人热情地端上来一盆蒸馍。也许,是真的饿了,就着泾川的本地小菜一口气吃了四五个。吃毕,才发现这蒸馍跟别处的不一样,馍底也是平的,但挺立如罐形,难怪主人用一小木方盘端过来时随口也说了一句:吃点罐罐蒸馍吧,垫垫底。罐罐,是西北一带对陶罐的叫法,听起来古拙而质朴,所以,罐罐蒸馍也有一股浓郁的山野之气。
据说,罐罐蒸馍发端于泾川的蓝家山一带。早在汉唐时期,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地带,过往商人常用水果、馍馍敬献神灵,祈求旅途平安。蓝家山一带的子民捕捉到些商机后,就拿当地的上等白面粉和面蒸馍,售与往来丝绸之路的商人。正因为罐罐蒸馍最初是以商品形态出现的,所以特别讲究色、香、形、味。有趣的是,不是泾川县到处都有罐罐蒸馍,只集中在县城近郊的水泉寺、阳坡、兰家山一带的几个村庄。所以,离开泾川,也就吃不上罐罐蒸馍。据说,罐罐蒸馍是这一带的祖传之物,靠的就是城郊这几个村子的井水。有人曾效而仿之,但模样总走形,蒸成软沓沓的碗状,而不能挺然凸立如罐。
蒸馍是西北人的家常之物,但做一锅罐罐蒸馍却非易事。
首先,面粉得选白麦粉。泾川盛产小麦,其小麦有红白之分,红小麦磨的面适合擀面,白小麦磨的面适合蒸馍。其次,工艺也很繁复,有和面、发酵、揉制、醒面、二次揉制等二十多道工序。听当地的一位老人讲,旧时磨面不易,妇人们闻鸡而起,吆驴套磨,用绸箩底的箩,箩面——箩底之细,肉眼几乎难以分辨。一锅好的罐罐蒸馍,最好是用这样的古法磨出来的面,细,有黏性,白如雪。当然,最关键的是其罐罐形状的决定,先要将其旋成下小上大、约四寸高的馒头模型,然后用硬柴架火,馍入锅后,火要旺,气更圆,蒸成,即为罐罐形。
这也是最为吃力的一个过程。
据说,一个不踏实过日子的女人是做不出来的,因为缺少了对生活本身的热爱。
相传,有一年康熙巡查宁夏时途经泾川,就吃到了泾川贡奉的罐罐蒸馍,吃毕,他大加赞叹:“天下扶麦之麦在泾川矣!”
罐罐蒸馍有一个好处,就是味道醇香,长期存放也不馊不霉。久存的罐罐蒸馍,倘若用开水一泡,如棉蕾试展,白莲初绽,加少许白糖,甚是好吃——若干年前,白面馒头很是精贵的那个年代,这样的吃法也是很奢侈的。在泾川乡下,罐罐蒸馍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可以当药用:长久存放的干馍,泡软后可以敷治一般的烧伤与烫伤。估计,现在已经没人用这样的土法了,毕竟,缺少科学的严谨。
读《泾川县志》,内有记载,几十年前泾川福音堂的一位美国传教士每每回国,总要带点罐罐蒸馍回去,分赠亲友。
这真是一位有意思的传教士。
□叶梓
相关新闻
- 2020-12-03初冬夜话
- 2020-12-03老屋里的时光
- 2020-12-03兰州地铁,不被辜负的期待
- 2020-12-03扶贫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