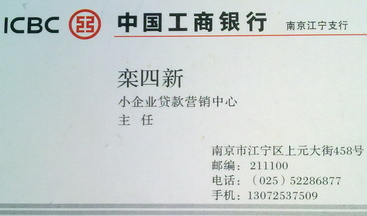悼念劳伦斯·费林盖蒂:点亮“城市之光”的书店主人
悼念百岁传奇老人劳伦斯·费林盖蒂
纸张可燃烧,但书店不会逃跑
点亮“城市之光”的书店主人 世界级文化地标的建造者
◎钟芳玲
很少有书店主人去世的新闻会上报,更别说是登在各大国际媒体了,但2月底,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法国的《费加罗报》《世界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等,全都大幅报道了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与出版社的创办人、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2月22日于书店附近的住家中去世、享寿一百零一的消息。短短几天内,我的电子邮箱和通讯视窗涌入了许多书友的信件与留言,大家同声哀悼。此时的我正在台湾,听闻旧金山的友人说要去书店凭吊,我请他们替我在书店前点一支蜡烛、放一朵花。
一个以读书、访书、说书、写书为工作和志趣的书女。曾任出版社总编辑、书店创意总监、香港国际古书展公关顾问等职。著有《书店风景》,是华文世界最先描绘西方书店的专书,另有《书天堂》《书店传奇》《四季访书》《访书回忆录》。
三易收养家庭
劳伦斯·费林盖蒂有个非常曲折的童年,他1919年生于美国纽约州,是个遗腹子,父亲是意大利裔的移民,在他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独力照顾他和另外四个哥哥,因压力太大、身心失调,在他两岁前进了精神疗养院。
费林盖蒂被送给一对未生育的亲戚夫妇,养父与养母感情不睦,养母不久就带着小费林盖蒂回到她的家乡——法国东部的史特拉斯堡,在那里住了几年,因此费林盖蒂最早能说的是法语,这也使得他日后对法国文化产生高度兴趣。五岁左右养母又带他回到美国,试图与养父修好。但不久年迈的养父失业,财力吃紧,六岁的费林盖蒂只能暂时被送到孤儿院。幸好较年轻的养母不到一年就找到工作,在一个富商家庭当家教,不仅食宿免费,还允许费林盖蒂同住。
当一切看似平稳之际,养母居然离奇失踪了,好在富商夫妇愿意收留他,成了他的第二家养父母,家中书房里的藏书也成了他的启蒙读物。谁知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引发了经济大萧条,第二家养父母家道中落,又把上中学的费林盖蒂托付给另一个家庭。
命运之神似乎不断和费林盖蒂开玩笑,所幸这两户人家都对他颇照顾,他也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甚至还获颁鹰级童军(美国童军的最高等级),但同一个月却因在小店偷铅笔被逮,这段可笑的过往被他写进了《自传》一诗中。如此坎坷的成长背景,想必和他日后特别同情弱势族群有关。
1937年费林盖蒂高中毕业,上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系,也开始投稿写作。据他表示,会申请进此校,是因为当时他所敬佩的作家汤玛斯·伍尔夫曾经是此校的学生。
1941年费林盖蒂大学毕业后不久,应募入伍海军,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6月,他指挥的猎潜舰参与了著名的诺曼底战役;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原子弹,同年9月中旬费林盖蒂随着美军踏上这片焦土。虽然当时尸体已被清光,但眼前却是绵延无际的泥泞,其中夹杂着大量的人骨与毛发。他经常在采访中表示,那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成了终生反战的和平主义者。
“城市之光”声名大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费林盖蒂以退伍军人的奖学金赞助,先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之后到法国索邦大学就读,于1950年底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51年移居旧金山,起初教法文、写艺评。1953年他与一位友人彼得·马汀各拿出500美元,合伙开了一家小书店“城市之光”,希望其成为一个文学聚集处。
书店所卖之书,偏向新潮、前卫、反传统、反主流,又特别关注小众、弱势、异类、异族文化,这里早期就卖起当时受歧视的同性恋主题相关书籍。此外,因为当时普遍认为好书皆是精装本,“城市之光”反其道而行,贩售平装书,成了美国第一家平装书专卖店。
由于书店前卫、自由、波西米亚的气息,早期吸引了不少后来出名的文青,如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盖瑞·史奈德等,这些人被称为“垮掉世代”。
1955年费林盖蒂买下彼得·马汀的股权,同年创立了与书店同名的小型出版社,首先推出了“口袋诗人系列”。以平装、小开本、廉价的形式出版诗集,第一本就是费林盖蒂自己的处女座《消失世界的影像》。系列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编号4、1956年出版的金斯堡诗集《嚎》(全名为《嚎及其他诗》,通称《嚎》)。
由于诗中涉及同性恋、嗑药与大胆的情爱字眼,诗集被警察没收,费林盖蒂被控出版猥亵书而被捕,后来上法庭审判,最终在支持者高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压力下无罪开释,2010年的电影《诗犼》(另译为《嚎嚣》)就是以此故事为剧情素材。这事件成了出版史上的里程碑,使得多年前的禁书也跟着解禁出版,例如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嚎》、金斯堡、费林盖蒂、“城市之光”更因此事件声名大噪。
1957年,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描写两位盲动的主角,无拘无束地在美国东西两岸间游荡来、游荡去的自传体小说,因作者以三个星期时间用打字机把稿子打在长30米的长轴纸上而备受讨论。当时已经颇具知名度的作家楚门·卡波堤在电视节目上接受采访时,曾以挖苦的语气说凯鲁亚克的书不是写作,只是打字。虽说如此,《在路上》还是得到许多年轻一代的认同,成了垮掉世代的经典之作。
虽然费林盖蒂宁愿称自己是波西米亚人,也不愿被归为垮掉世代,但他的书店与出版社却是孕育这群文青的关键场所,书店二楼也一直辟有垮掉世代书区。
当时在世作家销量最大的诗集
1958年费林盖蒂的第二本诗集《心灵的康尼岛》出版。一开始在声量与销量上无法与《嚎》相提并论,但诗句易读且带着魔幻、怀旧的浪漫气息。随着口耳相传与时间的推进,1989年在美国本土已经售出约70万册,若加上其他国家的翻译本,则达100万册。
《心灵的康尼岛》不仅成了费林盖蒂最受欢迎的作品,据称也是当时在世作家销量最大的诗集。这本诗集的书名其实取自亨利·米勒的诗《进入夜生活》中的一小句,整本书并未提到康尼岛,康尼岛是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半岛(原是一座海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是非常兴盛的游乐场,以旋转木马、摩天轮、马戏团、晶亮的夜景著称,费林盖蒂借由此意象表达他对整组诗的感觉,仿如心灵的康尼岛、仿如灵魂的马戏团。
1998年费林盖蒂被封为旧金山市第一任桂冠诗人。在旧金山新落成的公共图书馆受封典礼的演讲里,他当着馆长的面,直言批评新的图书馆比旧馆有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书架摆书的空间却比之前少;他还不忘呼吁市民投票反对重建数年前大地震震坏的市区高速公路,也不管当时的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就坐在台下,由于费林盖蒂的倡导,那段塌方处改成了绿林大道。
这么多年来,“城市之光”已不再局限于卖平装本,只要是他们认可之书,无论精装平装都欢迎,但精神与原则不变,一般市面的畅销书,如《五十度灰》或心灵鸡汤之类,绝不会在此出现。
书店虽然一直矗立在哥伦布大道斜坡上,但店面扩增,二楼窗户与外墙不时轮替出现费林盖蒂手写的大字海报,或是印制的长海报,针对社会政治文化议题发声,宛如诗人抒发意见的大型扩音筒与肥皂箱,也成了一幅幅流动的风景,例如“阻止战争与战争制造者”“打开门,打开书,打开心灵,打开心扉”。2001年旧金山市政府正式将“城市之光”书店与出版社列为历史地标,这也是旧金山首次以行号而非建筑登录。
两家因店主结盟的友情书店
上个世纪末我撰写《书店风景》时,慕名造访了“城市之光”,之后写了篇专文,许多读者告诉我,他们是因书中介绍,才认识了这家独特的书店与主人。
本世纪初我旅居旧金山后,平日常去书店逛逛,逐渐也和资深总采购保罗·山崎成了朋友,去书店时若正巧碰到健谈的保罗刚好有空,就会相偕去对面的“托斯卡”点杯马汀尼或咖啡谈天说地。保罗自1970年就在“城市之光”服务,没人比他更清楚书店和整体书业的起伏与变迁,书店有此老臣效忠,令人放心。
若与外地来访的书友相约,总选在“城市之光”会面。他们乐于到此“膜拜”,在店里买本书或印有书店名号的提袋,看看费林盖蒂手绘的标语与图画,到店外铺有镌刻诗句石砖的行人专用道“杰克·凯鲁亚克巷”上走走,欣赏书店和隔邻维威苏酒吧外墙的斑斓壁画,方觉不虚此行。“City Lights”已成了我和书友间的一个通关密码。“城市之光”的顾客少说有一半以上是外地来的“朝圣者”,老少文青们把此处当成必访之处。如果碰到费林盖蒂在书店发表新书,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好几次我都被挡在门外进不去。
费林盖蒂八九十岁时,我不时在书店、路上、咖啡馆或艺文活动上见到他。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11月7日那晚,在书店附近一间老剧场兼夜总会“富佳利俱乐部”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92岁的他戴着红色塑胶框眼镜、橘色围巾,穿着红色运动鞋,很帅气地与81岁的老友盖瑞·史奈德同台演出。我多年前曾两度与史奈德会晤并访谈,《书天堂》一书中有长篇介绍,因而倍感亲切与兴奋。这两位诗人是属于那种愈老愈有韵味的长者,朗诵会终场,两人神采奕奕地谢幕,群众欢声雷动。在我和其他出席者的心目中,他们俩才是最闪亮的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场诗歌朗诵会结束一个多月后,费林盖蒂的另一位老友、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于那年12月14日去世,高龄九十八,这又是一则国际媒体都争相报道的新闻。
惠特曼比费林盖蒂大六岁,同是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曾从军,也是靠着退伍军人的补助到索邦大学读书,他于1946年抵达巴黎,爱书的他还私下在学生间买卖二手书,费林盖蒂因到索邦求学而认识他。
1951年惠特曼在巴黎河左岸开了家书店,一开始名为“西北风”,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惠特曼将其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主要是为了纪念他景仰的前辈丝薇雅·毕奇女士。毕奇也是美国人,1919年在巴黎河左岸开了专卖英文书的“莎士比亚书店”,从此成为当时文人与艺术家,例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乔伊斯的聚集地,她还在1922年出版了当时英美不敢出版的乔伊斯的巨著《尤利西斯》,成了书业的传奇人物。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骚扰,毕奇在1941年关闭了“莎士比亚书店”。惠特曼沿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号,自许为毕奇的传人,同时也延续她雅好艺文的人文特质,甚至把书店当旅店,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文青免费住宿,蔚为奇观。
由于费林盖蒂与惠特曼的好交情与他们的共通理想,所以两家书店结盟为姊妹店,细心的访客会发现两家书店入口的大门上方写着对方的店名。两位年轻时相识的友人,双双在巴黎与旧金山开书店,并成了世界级的地标。我有幸先后与这两位传奇书人会面、留下文图记录,并收入第一本著作《书店风景》的前两章,也算是我访书与写书生涯的一大亮点。
书店永远漂浮着他的气息
近几年费林盖蒂已鲜少公开露面, 2019年3月24日是他一百岁诞辰,旧金山市政府宣告这天为“劳伦斯·费林盖蒂日”。书店的外墙上也挂起了艺术家派屈克·皮亚拉设计的五幅长型海报,海报下方印着他的一句诗,中文或可译为“纸张可燃烧,但文字会逃跑”。右边第一张画面是费林盖蒂拿着书本在朗诵,口中吐出一朵祥云。其他四张画面显示漂浮的书页渐渐成了纸鹤,最后化为展翅飞翔的白鸽,整个设计凸显费林盖蒂毕生倡导言论自由、不畏压制的风格。
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散发出一丝哀愁。费林盖蒂在生日前几天接受一位记者访谈时,表明了自己不会参加书店为他举办的庆生活动,因为他的视力变差,近乎全盲。但他生日那天,书店内外、杰克·凯鲁亚克巷、维苏威酒吧还是挤满了来庆祝的人潮。另有一小群粉丝则私下聚集在费林盖蒂住处楼下,对着站在二楼朝窗外探身的他唱起生日快乐歌,一则视频留下了这个温馨片段。
我留意到费林盖蒂脖子上还是围着八年前在富佳利俱乐部诗歌朗诵会上那条鲜艳的橘色围巾,只不过在旁人搀扶下,诗人以往的灵活与抖擞已不复见。然而令人振奋又感动的是,他在百岁这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小男孩》。这令我联想起杨绛、齐邦媛、叶嘉莹这些活到老还笔耕不辍的学者作家,或许就是创作的动力,给了他们能量,使他们延年益寿。
受到COVID-19的影响,旧金山的书店自去年3月中无限期停止营业,这对仰赖现金流通的“城市之光”冲击甚大。4月9日他们上众筹集资平台发出求救讯号,希望募集30万美元,帮助书店渡过难关,结果不到24小时就达标,四天募得46万美元,有9600人赞助,可看出“城市之光”受爱戴的程度。世道再艰难,“城市之光”不能灭,这家书店一定得支持,大家有此共同信念。
对我们众多书迷而言,费林盖蒂和“城市之光”是画上等号的,他的形体虽消失,但书店却永远漂浮着他的气息,店内随处可见他手绘的标语:BOOKS,NOT BOMBS(要书,不要炸弹),I READ,THEREFOR I AM(我读故我在),尤其是从地下室到一楼到二楼,都出现的标语“HAVE A SEAT + READ A BOOK”(请坐下,读本书),仿如诗人殷勤向你我致意。
小注
媒体关于费林盖蒂早期的生平介绍,往往在年代上有所出入,笔者参照各种资料后,选择以1990年出版的传记《费林盖蒂·他那时代的艺术家》为本,作者为贝里·舍勒斯基。
相关新闻
- 2021-03-22是“爆款”还是“扑街”,关键在于创作理念
- 2021-03-22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书院
- 2021-03-22在读书声中看见未来
- 2021-03-22军旅报告文学的审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