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晚清二十年》:用理性与温情走出悲愤、走近真实
《激荡:晚清二十年》:用理性与温情走出悲愤、走近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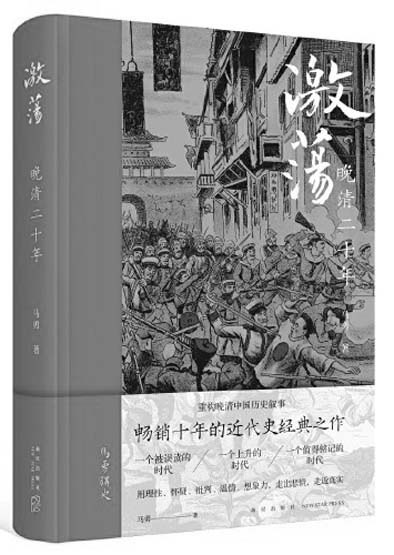
《激荡:晚清二十年》/马勇 著/新星出版社2021年出版
在《激荡:晚清二十年》中,我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能不能重构我们的晚清史。大致而言,几十年前,当我们这一代学者还没有出道时,我们的晚清史,不论中外,也不论两岸,其实都是一个叙事模式,都是将晚清视为后世中国发展的拖累,是后世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论我们去读台湾学者的著述,还是去读《剑桥中国晚清史》《哈佛中国史》《讲谈社中国史》,可以发现东西方学者的晚清叙事,都在强调晚清中国的悲剧意义。
就拿美国学术界来说,自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至其及门弟子、再传弟子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新清史”等各种各样的新视角,其对晚清中国的整体观感总体是负面的,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
对于这些中外前辈以及同辈时贤的研究,我始终心怀敬意,汲取甚多。只是我所接受的知识、信息,又让我几乎从一开始就不太认同传统的晚清中国历史叙事。我以为传统叙事太过于悲伤了,这个叙事看到了晚清中国受到的伤害,但也极大低估了晚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忽略了历史主导者的话语。
不论是清帝国的自我历史建构与描述,还是接替清帝国的中华民国早期对晚清中国的历史叙事,并不是以悲情为主基调。民国初年的中国人对于走过的路固然有反省,有批评,但总体而言对于晚清中国几十年特别是最后二十年的进步并不是完全抹杀,而是接续。就制度层面说,清帝国与中华民国固然是帝制与共和之别,但这个“別”用当时人的话说,是“国体变更”,是“君主立宪”与“人民立宪”的不同,并不是另起炉灶从头开始。那时人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用历史研究者习于使用的话来说,是社会性质在这连为一体的几十年发生了变化,而不是帝制结束之后的突变。
对于“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内涵与外延,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要从两个相互关联的视角解析这个变化。第一个视角,是时代性质的突变,是一个时代的觉醒。
我们今天都知道,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均不来自于中国内部,中国经过先前几千年的发展,在政治、社会、文化、教育诸方面,均获得了长足进步,如果我们去读大航海之后至十八世纪晚期长达三四百年间进入中国本土的那些域外有识之士的记录,大有几十年前福山所谓“历史终结”的感觉。中国的政治架构,根据利玛窦的观察,大致实现了西哲“哲学家治理”之模式,君主、大臣,以及帝国全境的大小官员,个个接受良好教育,彬彬有礼,上马打仗,下马治国,公平正义得以彰显,上下声音的传导反馈,更有机制性保障。即便是商业、贸易、城市生活,那时的中国,并不比东西洋落后。乾隆皇帝不愿向西人学习,他的自信有足够的理由,仅仅是凭借巨大的贸易顺差,他也有资格对强行入境贸易者说不。
但是,就在乾隆大帝对马戛尔尼说不的时候,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蒸汽机改变了世界,让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被迫卷入工业化运动。那时的中国有足够的贸易结余,乾隆皇帝那时如果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与英国重构国家关系,打开国门,自由贸易,像英国一样发展自己的工业化,那么十九世纪之后的中国史甚至世界史都会改写。然而,聪明过人的乾隆大帝并没有看到人类历史的趋势,不知道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中国错过了工业化的早班车,这一错就是一百年,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才不得不开始自己的工业化。
一百年的错失,让中国后来的步履几乎全乱。中国被迫开始自己的工业化之后,以为这个运动只是“坚船利炮”四个字,最多是“坚船利炮声光电化”八个字。因而那时的中国拼命追赶,集中一切精力、一切资源发展自己的工业化。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获得了巨大成功,重工业、制造业、交通、通讯,以及城市化方面都有骄人进步。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已走出半个世纪以来的困境,甚至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为世界经济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让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相形见绌,他们期望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但是他们的力量根本无法与清帝国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抗衡。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甲午战争之前十年、二十年的中国外交史,就可以深切体会列强面对想象的中国市场,贪婪而又无奈。这时的西方外交官已经不再有威妥玛、蒲安臣那一代人的想法,他们不是要引导中国走上世界,而是思考如何让世界进入中国。
中国的大门没有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而逐步打开,反而因中国实力增强而逐步关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这其实关系到我想说的第二个视角,也即传统与现代。
十八世纪的中国没有跟上工业化的节奏适时进入工业化时代,不仅错失一百年,而且使中国人的心理发生微妙变化。当中国不得不开步走向工业化时,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弯道超车。因而中国没有西方工业化发展初期自然发生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社会改造、阶级重构,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但中国的社会其实还处于传统时代,与现代社会并不吻合。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在工业化发生初期格外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不是从制度、文化上重构中国。
假如不是甲午之役后一切归零从头开始,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谦虚谨慎,增加向东西洋各国学习的力度、广度,逐步从经济增长扩展到教育重建、社会重构、军事再造,甚至制度方面的适度调整,那么中国后来的道路肯定不一样。
许多人会说,这是历史的假设而不是历史真实。其实,甲午后中国不就是沿着这些假设的路径进行调整的吗? 社会改造是一个整体工程,社会的进步必须拾阶而进,整体推动,而不能想当然地实现优势互补,不可能将马的速度与牛的负重完美结合起来。
甲午战争后中国付出的惨痛代价无疑是后世中国人永远不会忘怀的耻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甲午一役终于让中国人从酣睡中惊醒,终于明白什么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维新,新教育终于开始起步,新阶级终于出现。中国的政治架构也必然会随着这些新因素而逐步增加,逐步调整,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必然随着这些新因素的添加而逐步变为事实。
这本书就是描述甲午前后至辛亥前后中国的变化,用“激荡二十年”一语概括应该最为贴切。在经济上,甲午前中国是最典型的国家统制型经济模式,尽管开始了工业化、城市化,但这些几乎与社会无关,“盐铁官营”在新经济时代更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民间资本根本无法染指这些新经济。但是,经过甲午之役,中国市场被打开了,不十年,在那些通商口岸上就形成了一个孱弱却巨大的新阶级,必须承认经济基础依然是社会变动的根本。
在文化教育、社会重建上,也无不如此。中国的新教育是维新时代第一主题,一个与世界一致的现代教育体制开启了。传媒业也是如此,至甲午,新闻纸不仅有了与东西洋相似的新闻体制,而且短短几年,新闻成了一个行业,一大批人凭借着这个行业成名、就业、影响社会。
总而言之,晚清二十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起始阶段,一个与传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新阶段从这儿开始,中国终于开始从传统、从农业文明中出走。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代。(马勇)
相关新闻
- 2022-02-25《西行悟道》:与文明对话 让文化发光
- 2022-02-21茅奖作家张炜最新随笔集解析“唐代五诗人”生命际遇
- 2022-02-18《人生能有几回搏》出版
- 2022-02-18孙晶岩:用体育和文学与世界对话 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