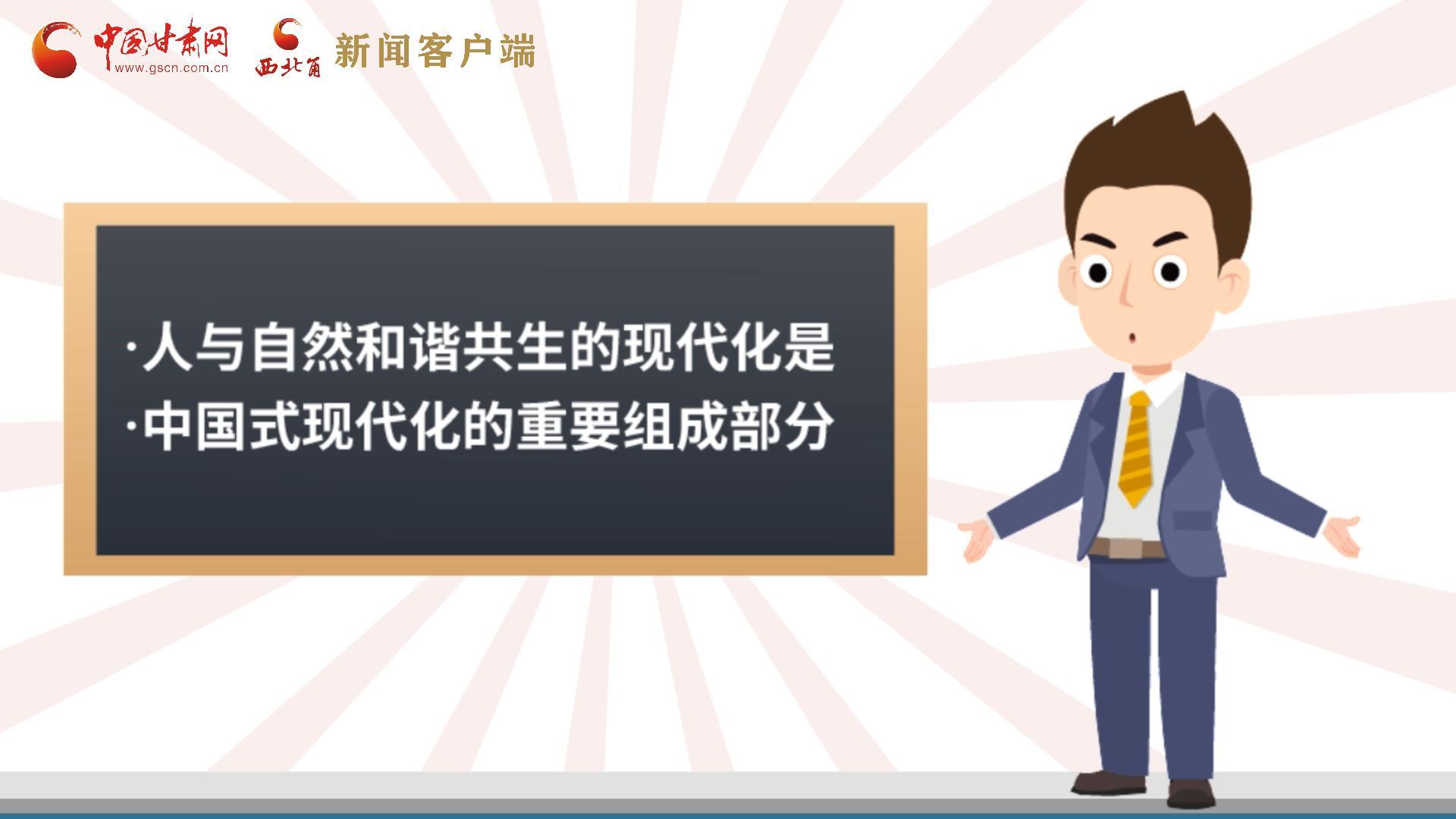读长篇小说《铜行里》:富有传统底色的沉稳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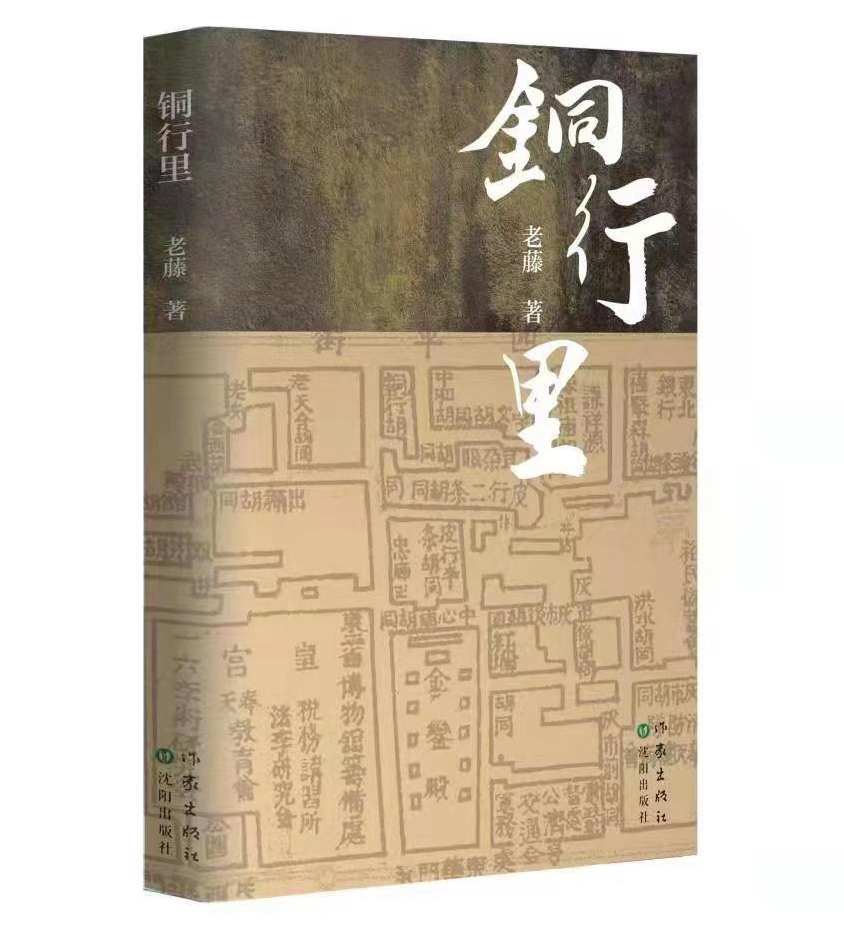
从文学履历上看,作家老藤属于一开始写作便有着明晰而坚定的文学理念和美学追求的作家。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潮流翻新更迭,阅读趣味的个性化和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构成了当代文学灿然而斑驳的文学景观。“变”成为常态。而老藤笃定地沿着经典现实主义一脉写下来,耐心地用扎实、干净的笔法状写脚下的大地、身处其中的生活,把那些目光所及的面容和风景妥帖地安放在一个个朴素、丰盈、好看的故事之中,而雅正蕴藉的中国传统美学也就隐身在文字的行间与故事的缝隙之中。
老藤的小说倾心于建构一个明亮、清正、善意的文本世界。大兴安岭之苍茫辽阔、纳谟尔河湿地的旖旎风光、街边摊上的鸡架杏仁粥……都被那个文学信仰照亮而熠熠生辉,又在充实、延伸着那个明亮的文本世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小说中的人物在世事变化中坚守、承续着恒久的精神与信仰。老藤的小说,每一部单独看是“独特的这一个”,放在一起又是彼此照应、彼此照亮的“互文本”组合,共同指向明亮之所在。这也是老藤小说抵达“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方式。
将长篇小说《铜行里》(作家出版社、沈阳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置于老藤的文学履历中不难发现,这部作品延续了他小说注重故事性、文化底蕴厚重、善用传统意象等共性特质,又在钩沉城市历史、挖掘传统文化精神等方面进行着新的拓展与尝试。老藤的小说与他切身的生活经历关联密切,即使是行使小说天然的虚构权利,也严谨地遵循细节真实的规则,这也构成其创作鲜明的在地性与及物性。《铜行里》是对他工作多年的沈阳近代城市历史的全景扫描。作品取材自始建于清朝皇太极年间的铜行胡同,以铜行胡同里富发诚石家、永和兴唐家、永昌号令狐家的兴衰与传承为主线,叙写了与铜器、铜行胡同相关的一百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在铜行变迁与个体命运的交织中折射出沈阳城的百年沉浮与文化底蕴。小说叙事时间跨越百年,中华民族百年的沧桑巨变浓缩于一条胡同的迎来送往、烟火生活中。
《铜行里》最吸引我的还不是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而是气场。小说通篇散发着一种处变不惊的沉稳之气。近代百年风云际会,在大历史帷幕下,铜行胡同也历经磨难,但始终不慌不乱,平日里本本分分,不显山不露水,专研手艺做好买卖;动荡时毫不含糊,披甲执刀走到历史前台,舍家为国在所不惜。这股沉稳之气的底色是小说中历代铜匠口口相传并亲身践行的“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这是传统的行业规矩,塑造了一代代铜匠的忠诚、仁义与敬业,也是一种稳定的文化秩序,是铜行胡同作为最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根基,更是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铜行里》是胡同小历史与民族大历史的一次不期而遇的碰撞,也是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文明意识的对话。
文学在虚实之间塑造着人们的记忆与想象,为读者提供了在虚构与现实之间参差对照、品读城市的空间。比如,作家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中苏州是否合乎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书页翻飞、口舌生津之时,苏州已经以色香味的形式沁入了读者的心脾。虽然铜器已经逐渐退出了当下的日常生活,但《铜行里》中那些关于铜器分类、制法、工艺、用途的细腻描写,已转化为情感记忆渗透在城市的文化肌理中,丰盈着城市的灵魂。琳琅满目的铜器是城市的美学肉身,那些萦绕在文本中的氤氲铜气,从历史深处发散出的灼灼铜光,犹如一个复古滤镜,为这座硬朗的工业城市打上了怀旧的柔光。《铜行里》用铜器激活了沈阳工业文化传统,也盘活了沈阳地图,从西瓦窑的古井开始,途经八卦街的回形楼、北市场的春饼店、北塔的法轮寺,沿着四平街、艳粉街、小北关街,过德胜门、来颖胡同,最后回到沈阳故宫北侧那条“长二百步,宽六步,北端接四平街,南端连着供奉关帝的中心庙”的铜行胡同。作者把这些古老的地标和街道集合起来,不动声色地安置在故事中,顺便把沿途的历史、风景与记忆编织起来,在铜行叮叮当当的劳作中唤醒读者的记忆。读者也跟随书中的路标,躬身入局,漫步在这座城市的文学地图中,感受北方一览无余的豁达与刚烈。
《铜行里》叙事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技法。小说以“楔子”开篇,“楔子”只有短短三页,不仅快速交代了铜行胡同的历史起源与传承延续,更以不容置疑的方式确立了铜行胡同的商业道德、精神信仰与伦理秩序。小说后面的各章都是对“楔子”的阐释与印证。正文部分以父子对话的形式展开,父亲石国卿给儿子石洪祥讲述与铜行胡同有关九十八个人的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框架。父亲承担了“讲故事的人”的角色,儿子是“听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是最古老的传播方式”。他认为,在席勒所言的“朴素的诗”的时代,讲故事的人通过不断的复述,呈现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讲故事是把故事融入讲故事人的生活之中,从而把故事当作经验传递给听故事的人”。讲述的故事既代表了讲述者的时代想象,也满足了接受者的心理期待,从而构成一种叙事共同体,共同承载一个群体的情绪与记忆。因此,无论是“楔子”所确定的小说主旨,还是一代代口口相传的“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以及从九十八人的软铜册到凑齐一百人的铜匠浮雕墙过程中的增补,一方面,在集体接力的传承中,普通人的世俗经验与道德讽喻被有效地固定下来,普通人的故事被赋予本雅明意义上的“光晕”,进入历史叙事;另一方面,普通人获得了讲故事的权利,带领听故事的人和读者一起,塑造历史,也重审自身。(作者:周荣,系辽宁文学院副院长,本文系辽宁省文联2022年度文艺评论重点课题“辽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研究”〔LWL202214〕研究成果)
- 2022-10-31富有传统底色的沉稳之气——读长篇小说《铜行里》
- 2022-10-31亘古放翁的隔世知音
- 2022-10-28《下庄村的道路》: 为“当代愚公”毛相林画像
- 2022-10-28为百年文学史中的“北京”留影——读《散文中的北京》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