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长在故乡的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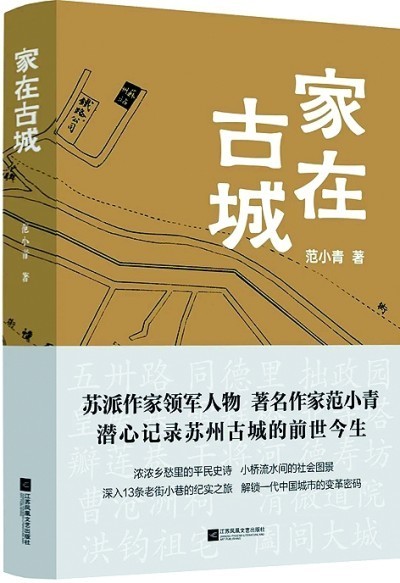
【文学里念故乡】
故乡是文学的土壤,文学是长在故乡的树。
我的文学之树,枝枝叶叶皆有情,这个情,就是对于故乡的感情。
我的祖籍是江苏的南通市,我出生在上海的松江区,与苏州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正宗的苏州人。
因为从三岁开始,我的根就扎在了苏州。我也曾经离开过苏州,比如在南京工作过,但是在那样的岁月里,不仅家始终在苏州,心中的牵挂也是无时不在。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南来北往都是客》,比较了南京和苏州两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虽然最后得出“苏州人,南京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客人”这样的结论,但是对于故乡苏州的偏爱之心,呼之欲出,太过显露,我甚至大肆地挑剔南京的饮食,认为南京除了一只鸭子,其他基本无甚可吃。
其实不只是南京,我对于苏州以外的美味佳肴,基本不能接受,何况,又何止是吃。诸多如此的执念,早已经深入骨髓,浸入血脉,改不了,摆不脱,就它了。
我喜欢苏州。
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说,现在仍然这么说。苏州松弛又机敏,苏州淡定却不“躺平”,苏州从容不迫、宽厚待人,又勤奋努力、争取进步。这就是苏州文化的双面绣。
因为爱,所以要去了解;因为了解,所以更爱。
苏州文化是江南文化的典范,颇具代表性,它源远流长,有着特殊性格,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爆发性的,而是弥漫着的,是绵长的,而且是有生长性、不断前行的。最重要就是它的普遍性,或者说是渗透性,它渗透在苏州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最普通的地方感受到苏州文化的影响。无论是达官贵人、才子佳人,还是普通百姓,无不与苏州文化融为一体。
苏州文化,既是高雅的,又是接地气、有烟火气的。时时处处,苏州文化都在启示你,给你灵感。
苏州有山,但是山不高,最高的穹隆山只有三百多米,且十分的秀气;苏州有水,但是苏州的水并不壮阔,是小桥流水。这样的山水养育的苏州人,性格是温和的,温和而又坚韧,静水深流,看起来柔弱,其实决不懦弱,是有力量的。在生活中,苏州不把精力浪费在无谓之争上。苏州的环境宽松、宽厚。在这样的环境中,苏州人勤恳地劳动,无论是“苏州园林甲天下”“苏州红栏三百桥”,还是今天的苏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样貌,都是苏州人辛苦创造出来的。这些都是我的故乡温和而努力的性格,对于我做人和为文有着重要影响。
就说说我们从小居住的苏州住宅对于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作用吧。
进门之前先抬头看看门上的匾,匾上的字,比如“厚德载物”,人的品德如大地般厚实,可以承载万物,一个有道德的人,像大地般宽广。每天进进出出,头顶上就是这四个字,会不会受到熏陶?肯定会的,多年下来,一辈子过来,你的道德文章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再比如“勤俭治家”,想必每天看到这四个字的人家,不大可能天天豪奢享乐。再比如“耕读传家”,这些人家的孩子,应该既会读书,又会做人做事。
良好家风,就在我家乡的街巷里,这样平平常常地展开着。说它平常,是因为到处都是,抬头可见,随时可遇,十分普及。
每天头顶着这样的意思,老话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想必潜移默化地影响生活在街巷里的每一个人。
还没有进门就已经感受到文化的影响了,再看看这匾上的字体、书法,要不就是厚实有力,要不就是刚劲挺拔,要不就是淡雅清新,这都是书法作品中的上品,是书法艺术的结晶,绝不会马马虎虎、潦潦草草,没有一点功夫的人,可不敢随便将自己的字放到人家的头顶上去。
走进去,看那些砖雕门楼、木刻,多么的精湛,多么的精雕细刻,这都是工匠精神的高度呈现,除了工艺惊为天作,内容上也大多是古代传统的、向善向上的传说故事,大多是有教化作用的内容。这又是一种文化的教益。
然后旧厅堂门前两侧的对联,比如“读书满座风云气,良友一堂富贵春”,或者“劲松迎客人同寿,清风满堂气自高”,这些内容,对自家、对客人的心情和态度,都是既积极又坦然淡雅的。
天井不在乎大小,在乎内容,梅兰竹菊,所谓的梅妻鹤子,恬淡、隐逸,超然物外。
现在,你们也许不同意了,如果江南人都躲在自己的街巷里、老宅里,这么淡然,那么无所谓,“闲饮窗前三杯酒,笑看堂外一树花”,这人生态度岂不是很消极?就不要进取了?这么没有追求了?
其实不然,老宅里这一切文化的体现和象征,看起来是淡然的,其实是有追求的,是有很多很大的追求。只是江南人的追求,江南人的努力,是低调的,不张扬的,是悄悄进行的。若不然,江南怎么会成为状元大户?
等等,现在你可能又有意见了,这说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宅子。其实不然,在江南的街巷,即便是普通百姓的宅子,也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
比如那许多沿河的平房,开门就是小巷生活,后门后窗是小河文化。行船、买菜,生动、舒展,和现在雷同刻板的高楼住房不一样,是生动新鲜的,是自然清新、接地气有人气的生活。
故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就成了我们人生的基础,也成为我们写作的依托。从故乡的人到小说中的人物,从故乡的风俗到小说的风情,无不深深地烙着故乡的痕印,无不来自故乡的馈赠。“陆苏州”陆文夫先生说过:“小说小说,小处说说。”这也是符合苏州性格的。故乡的文化还告诉我,在个人的东西中,必定有历史和时代的宏大,而宏大的东西,也必定体现在某个具体的人和事上。
从一开始,我就是讲着苏州故事进场的,从此以后,一直盘旋不离。尽管近年我的小说中较少出现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物符号,但是我作品的内在灵魂一定是苏州的。
说一个苏州故事,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嫁入豪门》。
大户人家后来日渐衰落。在“我”走进这些老宅的时候,它们已经面目全非了。
但是,宅子变了,遵守的东西没有变;物质毁了,精神依然在。这是一个老宅里小茶几的故事,“我”是故事的叙述者,但不是主角,故事围绕“我”婆家的一只鸡翅木小茶几展开,写了几十年来小茶几的命运,其实也是人的命运,是人的精神走向。
“我”嫁到宋家以后知道了鸡翅木茶几是一件值钱的东西,许多年来心里总是放不下它,一心想把它变成“实用”的东西,但是我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我”曾经和“老宋”、和“老宋”的母亲聊天,坐在阴湿的老屋里,面前的小天井零乱而又宁静,堆满了杂物却没有一点燥气。他们对一去不复返的从前生活没有更多的感叹,他们对老宅外喧嚣繁华的世界也没有过多想法,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自己的那一份日子,延续着家族留传下来的某些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
小茶几只是老宅中一件很细小的物品,是小到可以忽略的。它既是物质,又不是物质。当它被当作物质的时候,它经常易主,命运一波三折,可以被搬来搬去,可以被人长年觊觎,一生惦记,它曾经去过冯爸爸那里,又去过古董店,最后到了小一辈的新房里,也许它还会更换更多的地方和主人。而当它呈现出非物质性的时候,它是永存不变、岿然不动的,无论将它搬到哪里,无论它的主人更换成谁,它的非物质性永远笼罩和弥漫在时空里,谁也看不见、摸不着,却有着无限的能量。
这是苏州文化对苏州人的影响,也是苏州文化对苏州文学作品的影响,它不是没有欲望,也不是没有动摇,但是终究会坚守着该坚守的东西,终究相信有一种力量永远都在。
《嫁入豪门》是苏式的,小说的画面是苏式的,“他们家的天井真是很小,院子的墙壁斑斑点点,有发霉的青苔,还有一些不知什么枯藤爬在上面,只有一棵芭蕉,虽然不大,却是长得郁郁葱葱的。他们家的屋子也很小,三间屋子都很拥挤,里边堆满了乌七八糟的旧家具破烂货,也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他们家的人就在那些东西的夹缝中钻来钻去,而且他们的动作很轻盈,幅度又小,都是无声无息的……”
小说的人物是苏式的,“我刷了牙,把牙刷朝杯里一插,他看了看,就把它倒过来重新插到杯里。我看不明白,说,你干什么?他又慢条斯理地说,小冯,牙刷用过了,要头朝上搁在杯里。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牙刷,说,为什么?他说,牙刷头朝下,就会一直沾着水,容易腐烂,容易生菌。我说,把茶杯里的水倒干了,牙刷就浸不到水了。他说,倒得再干,也总会有一点水积在杯底。我说,这是你们大户人家的讲究?他说,无论是什么人家,都应该这样的。等我洗过脸,挂了毛巾,他又过来了,我赶紧看看我的毛巾,我那是随手挂的,等于扔上去,当然是歪歪扯扯。他看了后,就动手把毛巾的两条边对齐了,然后退一步看了看,又再对了一下,那真是整整齐齐了。我说,怎么,两边不对齐容易腐烂吗?他说,不是的,两边不对齐,看起来不整洁”。
小说的细节是苏式的,小说的对话也是苏式的。在这里,苏式无处不在。苏式,是一种情绪,是一种生活形态。而在小说作品中,苏式又是写作的一个诀窍,是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
由一个承前启后、中间时段的人物,牵连起苏州大户人家的命运,“我”,既往前走,又往后看,“我”的眼睛和脚,走过了这一段历史,也走进了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之中。
我们不能摆脱物质、丢弃物质,但是我们又不甘心被物质所束缚。于是,我们困惑,我们迷茫——这就是小说中的“我”。
将这样的困惑,这样的迷茫,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这是我们当今写作的价值体现。而它的精神实质,既是苏式的,又是现代的,这就是苏州文化的生长性。
最后抄录我在长篇非虚构作品《家在古城》中写下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这一次的采访和写作,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在苏州古城面前,我要再用一遍我已经用过数次的话:它们所容涵的博大精深,恐怕是我穷一辈子努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
于是,在我的文章里,我在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段落,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句子里,都埋下了烟花,如果有人愿意,或者我自己愿意,点燃这些烟花的引索,它们将绽放出无数绚丽无比的画面。”
(作者:范小青,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 2023-09-04《诗经》记录的先秦爱情与民俗
- 2023-09-04缭绫何所似
- 2023-09-04评儿童小说《完美一跳》:有质感的成长书写
- 2023-09-04研讨阿乙《未婚妻》 重启“文学京彩季”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