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诗存史:白族女诗人寻踪

周锦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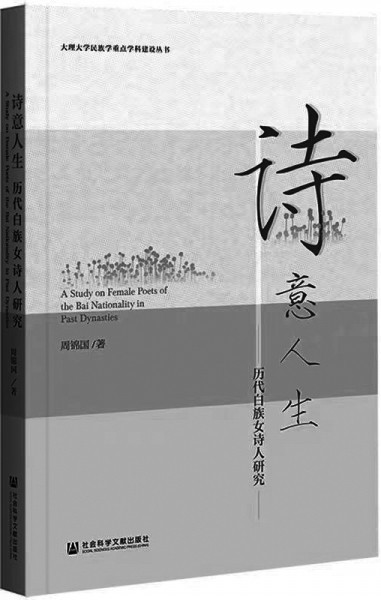
阅读提示
《诗意人生:历代白族女诗人研究》聚焦从元代到民国大理地区的23位白族女诗人及其作品,解码在特定历史时期白族女诗人群体的构成、创作成因、主题演进、创作特色、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是一部诗学视野下白族知识女性的精神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该著作既体现了女性诗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也彰显了白族女诗人之于民族文化记忆的构建意义。
■ 陈辉 田泥
在古代文学史上,诗歌向来就被看作是男性的舞台,少有如李清照等这样能突破性别偏见藩篱的女诗人,进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之中。这就导致,知识女性在克服传统社会种种困难之后,她们的文学表达依然难以被注意、记录、保存和流传,后世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往往需要从众多史料之中去钩沉、裁选、考订出一些“只言片语”,以此打开被深锁在历史空间中被忽视和低估的女性集体记忆,来感知作为人类世界一半女性的心灵、情感和思想世界。此种困难可想而知。周锦国的《诗意人生:历代白族女诗人研究》则是一部专门对大理地区少数民族女诗人研究的成果,该书将“女性诗人”这一视点放在边疆少数民族,聚焦有史料所载的23位白族女诗人及其作品,解码在不同历史时期白族女诗人群体的构成、创作成因、主题演进、创作特色、审美价值与社会意涵,是一部诗学视野下白族知识女性的精神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部白族女诗人的精神文化史
本书作者在分析、考释白族女诗人群体精神文化构成因素时,首先对她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以人系史,揭示出了影响她们诗词创作上的主要外在因素。白族深受儒家汉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汉文化之间经常有着很密切的互动和融合,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白族女诗人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从南诏大理国时期到元朝,再到明清时,儒家文化的道德体系和规范,逐渐成了白族知识分子们的主流,直到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建立和新思想的涌入才发生变化。
这一渐进的过程体现在女诗人诗歌里就形成了一种“过渡—成熟—再过渡”的总体艺术特征,主题和审美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早期高夫人、阿盖等人的诗歌内容里,白族地区的风物、历史和语言占有着较大比例,呈现出一种过渡时期文化交融的特色;及至明清时期在周馥、苏竹窗等人的诗中,这种过渡色彩就已经褪去,白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和汉文化历史传统在诗歌表达上已然变得浑融和成熟,并有着大量的儒家汉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念,儒家文化占据了主体;而到了清末民初,跟随儒家文化的际遇,在白族妇女们的诗上又体现出了过渡时期的特征:既有着如杨熊氏、杨周氏、蔡吕氏等为坚守忠贞而殉节的绝命之语、李培莲温柔敦厚的儒家风格之言,又有着如章青昔《五月农人》等充满强烈反思意味和平等观念的现代之思。
当然,除了汉文化浸染这个社会文化因素以外,内在家庭动因如家学渊源、家庭角色分工等,也是影响白族女诗人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白族女诗人或学诗于家中长辈,或学诗于丈夫,亦或本身就生长于教育世家。丰富的家庭文化资源是她们得以写诗的文化基础,但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的认同,也使得她们的诗通常囿于家庭之内。夫妻唱和诗、爱情诗、思夫诗、家庭日常生活感事诗、写景咏物诗、教育诗等占据了她们诗歌的绝大部分,只有周馥、袁漱芳、李培莲等少数几人展现了对历史、社会政治现实的纪事、思考和咏叹,但这些作品在她们的诗作中也并不占多数。
顺着这样的精神文化构成的逻辑追索,作者对白族女诗人及文本所呈现出的精神质素,进行更为纵深地解析与判断。采取的策略就是将白族女诗人的诗歌创作,纳入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加以观照,尽管还没有提供更具翔实的诗作文本比照分析,所涉及的文本细读与意义挖掘还显粗糙,但也大致阐明了白族女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与中原地区女诗人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展示了她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白族知识女性内在精神空间的构筑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白族女性,其诗作在思想内容、情感体验和精神表达上与中原地区女诗人的作品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我国古代女诗人在诗词创作上所表现出的跨时代共同主题,诸如闺中相思、弃妇忧愁、感物伤怀等,在白族女诗人中多有体现,她们同样以家庭生活为核心,叙述对外出丈夫的思念以及家庭生活情景。例如苏竹窗的《听砧》:“秋气肃然重,邻砧入听才。夜随凉月静,声带暗霜来。乍断知无力,连敲觉有哀。感余难遽寐,半晌倚妆台。”此诗描绘了因听见石砧上敲打声所引起的孤寂悲凉,写得极为精妙和富有表现力,已然具有大家风范。一同宣扬儒家妇道规范的诗亦有不少,如周馥的《课二女迎寿、双岫》:“女终伏于人,坐绣平心性。一月四十五,日轮牵得定。”此诗既是教育女性应当品德顺从、吃苦耐劳的典型,也蕴含着诗人夫子自道之感。
此外,非功利性的个人情怀抒写,在特定历史时期书写家国时事与抒发家国情怀,也是她们的共同之处。不同于男性写诗往往带有交流或传世的意味,女性诗歌的欣赏对象通常只限于家人和少数几位好友,这使得她们的诗作更多的是个人情怀的真切抒发,显得更自然,更有诗意特征。而在社会动荡、转折之时,她们当中富有卓识者,也能写出具有深切家国情怀的作品,表达自身的忧国之情与社会之思。像李培莲的《春光》一诗:“迭遭烽火后,无复锦官城。草木千丛绕,春光百战经。村烟皆断绝,华屋长榛荆。一片荒凉景,何时见太平?”于写景之中寓以社会现实,表达出对社会时事的关切和对太平盛世的企盼,即是此中佳品。
但大理毕竟处于边疆,白族自身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习俗风物,其位置也与佛教文化区相接壤并有着深厚的当地佛教底蕴,故其文化上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主,但也呈现出多种文化相交融的色彩,反映在女性的诗作中则体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和兴味。首先是对大理自然、风物等的生动表现,如苏竹窗对大理定西岭的描写,起句“佳气莽无边,横来半壁天”(《登楼望白崖定西岭诸山》)就展示了此山雄壮的气势,而另一句“马背千盘路,林梢百丈泉”就充分突出了大理山形特色,颇具地域色彩。其次是不乏当地佛教教义的思考,如周馥的《雨铜观音殿示同游诸娣侄》中“都是空三法,最难灭一嗔”等句,以诗的语言将自己对佛义的参悟道出,尽显高妙。最后是在日常世俗空间中审美特性上更加“坚韧”,白族女诗人虽然也经常表现闺中相思、弃妇忧愁,也会感物伤怀,但很少具有“闺怨”气、“柔弱”气,尤其与江南女性诗人相比,更显边疆少数民族女性的坚韧和刚毅,“瘦”“病”“愁”等古代女性文学常用词在她们的诗作中几乎难以见到,周馥《紫笈夫子就馆中甸话别》:“唐破吐蕃地,夫君又远征。铁桥江漭荡,石鼓雪峥嵘。翁殁新阡表,姑衰宿疾萦。家贫无一可,辛苦砚田耕。”一诗就是很好的例证,此诗叙写在丈夫即将再次踏上远行之路之时,尽管家中依然贫困,公公新近离世,婆婆又疾病缠身,但她不仅没有抱怨,反而展现出惊人的理解和包容,以无畏的勇气面对生活的艰辛,生动显示了边疆白族女性的刚强品质。
我们也不难发现,白族女诗人全部都使用汉文创作,在诗歌中经常出现对中华民族历史和古典文化的引用与借鉴,通过诗歌表达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认同和记忆,如袁漱芳《春燕》一诗中有“白玉楼高身可寄,乌衣国远梦能通。上林如许春光好,待尔飞鸣御花中”,就连着化用了“白玉楼”“乌衣国”“上林苑”三个中华历史典故来表达自身的思想感情,充满了历史记忆和文化韵味。可见,白族女诗人不仅展示了自然生态、家庭文化、生命经验与心灵世界,也传承了传统文化,构筑了女性集体记忆和大理边地的文化景观,这对中华多民族文化融合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母体文化的重建,同样具有非凡的价值与意义。
总体来看,这部诗学视野下的白族知识女性的精神文化史的搭建,其本身所提供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本书作者其实就是沿用了经典的文学史写法与框架,然后把文本及史料装载,加以对边地白族女诗人与中原女诗人诗作的风格等比较和总结,侧重于把白族女诗人与民族文化、中华母体文化关联重点梳理。而对于白族女诗人所表达的传统性别文化结构对白族女性钳制与束缚以及她们自我内在精神空间的构筑等,该书并不作为重点聚焦与挖掘。诸如野史中对高夫人唯一诗作遗存的肆意增改,从而将高夫人弱化为男性诗人笔下的“怨妇”等事件以及数量上不少的因固守忠贞而“殉节”的女性绝命诗、决绝诗的存在,作者在谈论这些绝命诗、决绝诗时,对她们的历史处境与生命遭际抱以理解和深切的同情,也侧面指认了深受传统封建文化思想控制的白族女诗人的“殉节诗”本身就是对历史发出的控诉。
白族女诗人所书写的对身体、身份与精神多重禁锢的抵抗之声以及形塑的自我形象与文化载体之诗作,都成就了看似不具有现代性别主体想象,却有着可信的女性存在的历史史实与文化镜像。因此,尽管作者并没有完全从性别文化视角说明:白族女诗人所有的历史情感与精神处境是叠合在男权中心文化场域之中的,混杂着一些对传统封建文化秩序的认同与妥协。但作者进行史海钩沉,让女诗人群像浮出地表,这就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与理论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 2024-03-18《唤醒:从人类、后人类到超人》:未来的人类如何生活?
- 2024-03-18国内首家地图主题特色书店青年之家揭牌
- 2024-03-14离白塔最近的书店开门迎客
- 2024-03-12从舞蹈史的角度研究古代文明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国甘肃网微信
中国甘肃网微信 微博甘肃
微博甘肃 学习强国
学习强国 今日头条号
今日头条号











